研究 | 李修建: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雅俗观(三)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5-11-10 浏览量:132
三、宋代以来的化俗为雅
字书对“俗”字的解释,大约有如下二义。一是习俗、风俗之俗,《说文解字》释“俗”为“习”,“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王教的目的在于移风易俗,促成美好社会。二是世俗欲望,《释名》释为“欲也,俗人所欲也”。因俗人为平民百姓,社会地位较低,贵族阶层高高在上,掌握话语权,所以“俗人”的趣味、理想往往会被看轻,在道德、审美等层面受到贬低。“俗”遂亦有了低级、下流的贬义。
整体来看,先秦时期推尊礼乐制度,其目的是以上化下,塑成淳美的风俗。风俗意义上使用的情况较多,尤见于“三礼”。《苟子》中有俗人、俗儒、雅儒、大儒之分,区分标准是其人是否掌握学知识,言行是否遵守礼义,是否信奉儒家理想,以及为政能力之高下。俗人不学无术,追逐利益;俗儒略通儒家知识,却不尊守礼义,以口舌讨衣食;雅言行崇礼,尊贤畏法,可辅千乘之国;大儒更上一层,能力最强,能令天下一统在这一分类体系中,雅俗尚非一单独的对立范畴。东汉王充的《论衡》中,田婴迷信流言,认为五月出生的长子有妨父母,被视为“俗父”,田文(孟尝君)则力辟之,以其德行才能赢得后世称扬,被称为“雅子”。雅俗对举,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
从中国文化史来看,先秦两汉时期,雅所代表的是宫廷美学的审美取向,宫廷美学以礼乐制度为基础,旨在维护中央一统的帝王尊严和上下有别的社会秩序,雅乃“正”之意。与之相对的,并非俗,而是淫、邪,有违礼乐制度,对社会秩序造成消解或破坏的郑卫之音、“夷俗邪音”及至魏晋时期,以阅读经史子集、偏好琴棋书画为特点的文人文化体系得以确立,知识与趣味塑造了文人之雅。魏晋六朝乃至唐朝,整个社会以门阀世族为主流,世族自身形成一相对稳固的共同体,既是政治共同体亦是文化共同体,寒门庶族很难跨越门第区隔。所谓“世胄高位,英俊沉下僚”。所以文人群体的交际圈局限于世族子弟,他们高高在上,相互品藻人物,清谈析理,比较高下,务求高雅,却极少面对俗的问题。雅俗并称的情况很少,只在《文心雕龙》中有三见,分别为“隐括乎雅俗之际”“情交而雅俗异势”“泛举雅俗之旨”,对于其涉及的确切内容,刘勰并未展开论述,实因雅俗问题在当时并不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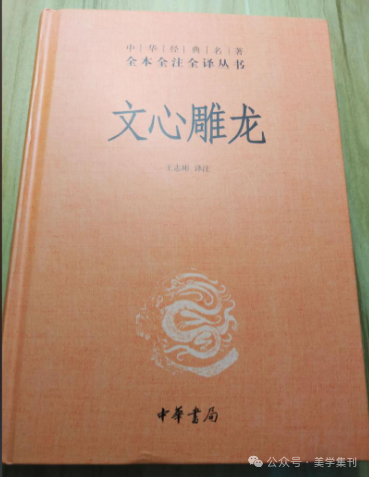
宋代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重大转型。科举制度使门阀政治彻底解体,世族退出历史舞台,为平民敞开了晋升之途,大批出身寒微的文人成为宋代政坛的领袖。运河与海上贸易、货币制度的改革等诸多因素,促进了宋代经济的繁兴。汴京、杭州等地,工商业辐辏,娱乐业发达,瓦子勾等娱乐场所在在多有,唱曲、说书、小说等通俗文艺兴起,孟元老亲身经历了汴京的繁华,他在《东京梦华录》自序中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大批低层文人投身其中,市民阶层以及市民文化自此蓬勃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宋代文人地位很高,精英意识很浓厚,他们自觉保有对雅的追求,将魏晋以来形成的文人文化体系进一步发扬光大,并以此形成文人共同体在文化趣味上与世俗相区隔。除了琴棋书画,宋代文人还将日常生活进-步精致化,发展出“四般闲事”,即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并赋予它们雅的内涵。此外,他们对于世俗生活,也能坦然接受,并将其雅化。他们不仅爱好写诗,亦热衷作词。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晏殊、辛弃疾等宋代文坛中知名的文人,亦都是词坛高手。宋代文人喜欢交游,茶坊酒肆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建构了新的文化空间。《梦梁录》载:“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流)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一方面是上层文化的下移,文人开始流连于市井,另一方面则是底层文化的提升,市井积极吸收上层文化的元素。
雅与俗,同时呈现在宋代文人身上。宋史专家邓小南等认为:“在宋代趋于平民化的大环境之下,'雅俗兼备’、精致与俚俗互通,成为时代的突出特点。”尽管雅俗兼备、雅俗互通,但宋代文人往往以其才情和趣味化俗为雅。这在诗论中多有体现,苏轼提到:“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亦有类似意见:“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以饮食为例,普通的粗茶淡饭,如竹笋之属,苏轼黄庭坚等士人为其赋予了风雅的韵致。苏轼在《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中写道:“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平凡之物,因为淡泊而空明的情感的契入,便附着上了高雅的意味。
降及后世,尤其是明代中后期以后,江南地区商业文化日趋繁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文人经商的现象不在少数。明清时期的文人,受到世俗文化的浸染日深,他们对待市井文化时出现了颇为不同的心态,有的积极拥抱世俗生活,甚至刻章张扬自己的世俗欲望,如袁宏道《感怀诗》所云“山村松树里,欲建三层楼。上层以静息,焚香学薰修。中层贮书籍,松风鸣飕飕。右手持《净名》,左手持《庄周》。下层贮妓乐,置酒召冶游。”在三层楼中,精神生活与物质享受并行不悖。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声称自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好变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其对声色的喜好更带有张扬与炫示的意味,有的则不无矛盾,透出焦虑,极力地在雅俗之间划出界线,以彰显自己之雅。
对“雅俗”的讨论在这一时期最为普遍,见诸文艺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居室而论,明清时期,大量文人对家居设计做过论述,如文震亨屠隆、黄图、李渔等人,有的还亲自设计图样。黄图在《看山阁闲笔·制作部》中谈道:“儒者风味,清而不浊,雅而不俗。”“制作不必好奇,务在求雅”,极力渲染文人的高雅趣味,然后指出,制作器物的目的,是希望“超脱时习,不类庸流,庶不没者之本色耳”。黄图设计了26种器物的图样,器物涉及门、帘、桌、椅、匾额,甚至还有便桶。这些器物,皆为日常之用,作者却务求别出心裁,追求雅致、雅观。对于日常交往的对象,他们要分出雅俗清浊,提出“毋对俗客”,在他们眼中,“富豪势宦,滑吏笔刀,啬夫利徒,忍人说士,以及伪学书呆,俱为俗客,如一感触,必致有污泉石而玷琴书矣”。这些人之所以俗,评判的标准不是政治地位和经济能力,而是以琴书自娱的林泉之心,亦即文人雅趣。
结语
从中国文化史的宏观视野来讲,“雅”作为一种审美趣味,其践行的主体,经历了从宫廷至文人的变迁。先秦至两汉,宫廷审美占据主导地位以儒家崇尚的礼乐制度为思想指导,宫廷所崇之“雅”,代表了中正和法度。魏晋之后,文人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掌握了文化话语权,文人所崇尚的雅,更多浸濡了道家风味,追求超逸、自然、淡远、拙朴。宋代以后市民社会兴起,俗的东西成为日常,进入文人视野,雅俗之辩成为重要话题。文人在面对俗的现象和对象时,往往以自己标举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品位化俗为雅,与他们眼中的俗形成区隔,拉开距离。
从文化相对论的视角来看,民间文化之“俗”,乃是因应市井百姓的审美需要,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是其必然。民间文艺,根植于民间日常生活的土壤。作为小传统的民间“俗”文化,与上层文化、文人文化并非相互隔绝,它一方面会积极吸收来自宫廷文化的内容或元素,如组织体系、价值观念等;另一方面,它时常通过调侃、戏谑文人文化,获得自身的价值认同。在看待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跳出雅俗之辩的精英主义立场,持一种平等的价值观,去发掘民间文艺“俗”的魅力。
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主编、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中国美学、艺术人类学。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美学集刊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