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李修建: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雅俗观(二)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5-11-08 浏览量:206
二、文人尚雅的四个维度
文人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汉末魏晋时期。魏晋文人大多出身贵胄,身居政治高位,经济条件优渥,受到良好教育,文化素养颇高。更重要的是,在此纷纷乱世,玄学成为思想主流,士人们莫不高倡老庄,热衷清谈,“越名教而任自然”。当时固然有“清谈误国”之讥评,不过,另一个事实是,中国历史上诞生了一大批极富个性、高扬情感、醉心文艺、风姿各异的文人群体,他们开启了中国文艺的自觉之路,促成了书法、文学等艺术的高峰,并且确立了中国文人文化体系的基本样貌。后世文人,不仅奉魏晋文人为楷模,其洒脱风度令后世追慕不已,更在其开启的文化体系之中沐浴成长,后世不过是在此基础之上有所修补而已。
魏晋文人开启了雅文化,也为中国文人赋予了崇雅的审美偏好。中国古代由雅组成的词语甚多,如高雅、典雅、古雅、博雅、文雅、秀雅、温雅、儒雅、俊雅、风雅、端雅、恬雅、淡雅、清雅、闲雅、和雅、雅致雅韵、雅人、雅量等。下面撮其要者,展开分析,
第一,以博学为雅。
中国古代,尤其是印刷术广为普及之前,以书籍为载体的知识乃稀缺资源,真正有机会读书并接受教育的人为极少数。周代以前,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接受“六艺”之教。孔子开创了民间讲学的先河,有教无类,他的学生之中,有一些出身低微的下层民众,但数量极少。汉代,伏氏家族和孔氏家族靠着对儒学知识的垄断,变文化资本为政治资本,世代为官,成为世家大族。东汉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蔡邕与王朗,先后得到王充所著《论衡》,学问大进,奉为至宝,秘藏不露。西晋张华,饱览群书,博学多闻被世人推崇备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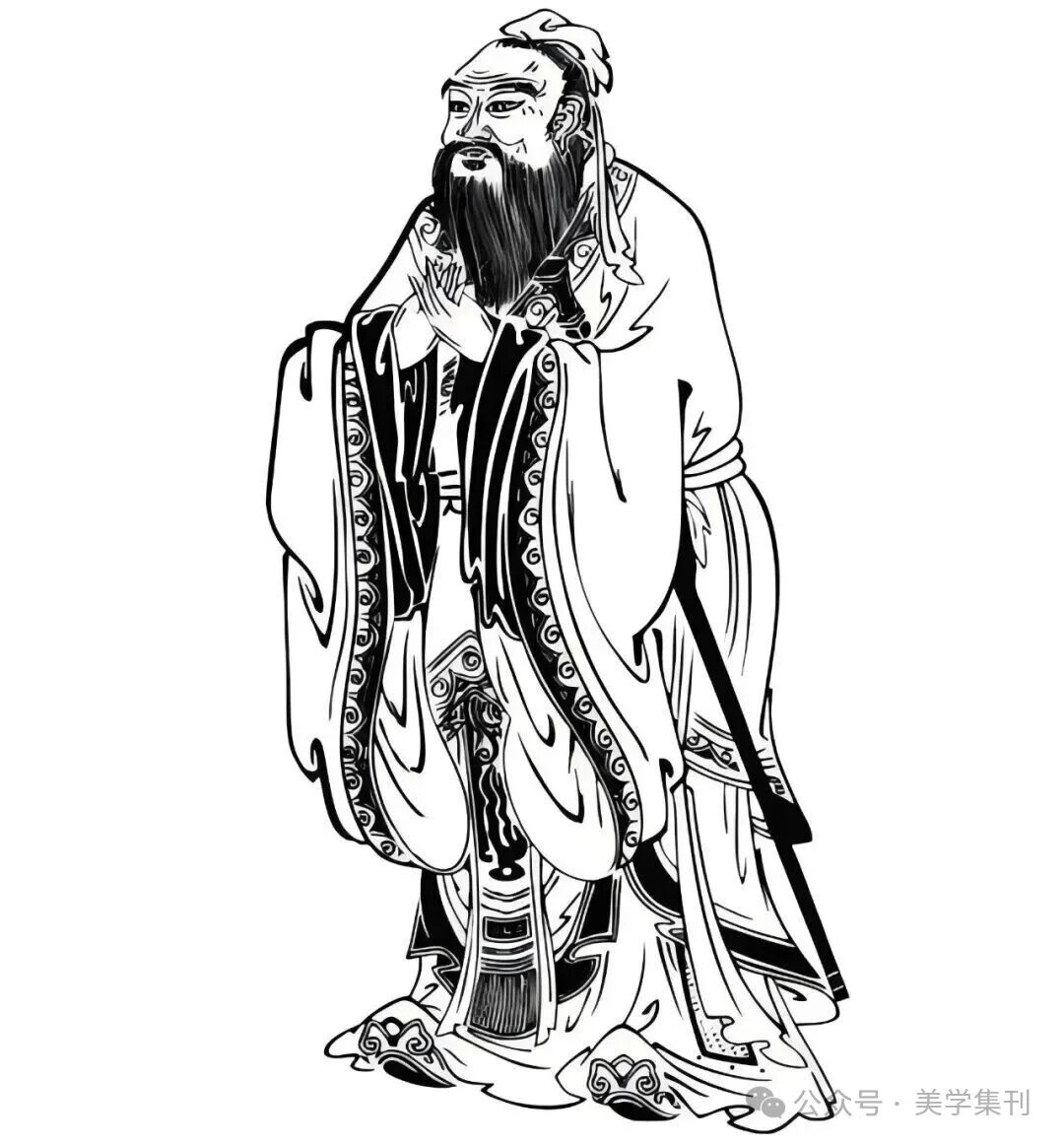
魏晋以后的文人阶层,其文化素养的表现之一,便是博览群书,以儒家为主的经典著作自是必读书目。除此之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各种杂学,都应在阅读之列。
博学之士之所以受到推崇,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其一,如上所述,知识为稀缺资源,为少数人所有,掌握了知识,就拥有了话语权,并可能由此获得政治身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即源于此。
其二,知识是社会区隔的重要方式,雅俗之分往往由此。掌握类似知识、具有相同趣味的人,往往分属一个阶层,形成共同体,并以此一知识与其他阶层相区隔。
颜之推《颜氏家训》中专门有“勉学”一篇,其中提到,士大夫子弟当致力于学问,否则,“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不学无术,就难以与他人交流,无法融入士人群体之中。宋代田锡在《贻宋小著书》中提到:“数日论文,更得新意;若获秘宝,如聆雅音。”二人讨论文章,屡获新意,很有所得,所以称其为“秘宝”“雅音”。明代屠隆在《画笺》中主张:“古画不可出示俗人。不知看法,以手托起画背就观,绢素随拆,或忽慢堕地,捐裂莫补。”普通百姓,无缘得见名画,更无从学习观看之法,因此屠隆强调不要以古画出示俗人,以免损坏。凡此,皆属此类。
其三,读书能增长见识,拓宽视野,开阔心胸,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在中国古代,无论哪门艺术,都不单纯追求技艺,而强调要多读书,通过读书提升人生修养与艺术境界。明代的沈野有言:“凡百技艺,未有不静坐读书而能入室者。”松年在《颐园论画》中提到:“画师处处皆有,须分贵贱雅俗。不读书写字之师,即是工匠,其胸次识见平庸,惟守旧稿,心模手追,老于牖下,有毕生不出乡里者,目未见名山大川,耳未闻历朝掌故,此等人断不可师法者也。”工匠不读书,没有见识,所以是俗人,作品亦是俗物。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书卷气”和“士气”,成为文人推崇的对象。清人王概在谈及如何脱俗人雅时提到:“去俗无他法,多读书则书卷之气上升,市俗之气下降矣。”所谓市俗之气,就是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庸庸大众所具有的精神面貌,这些人无暇或无缘读书,身上没有书卷气。清代王原祁提出:“画法与诗文相通,必有书卷气,然后可以言画。”在古人看来,只要多读书,就会有书卷气,作品也会相应地呈现书卷气。董其昌提倡文人画需有“士气”:“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似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草隶奇字之法,凡夫难以掌握,文人却正有研究,以此为画,自然与众不同。汪之元还提出了“文人之笔”:“雅者有书卷气,纵不得法,不失于雅,所谓文人之笔也。”
无论是书卷气、士气,还是文人之笔,所指向的审美趣味都是雅的。宋元以来,对文人画和院体画的区分,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文人画带有书卷气,绘画者多是博雅、渊雅之人。
第二,以超逸自然为雅。
冯友兰先生写有一篇名为《论风流》的文章,他认为,风流是二种人格美,真正的风流,需要四个方面的素养:玄心、妙赏、洞见、深情。四者之中,将“玄心”排在最前,是有道理的。冯友兰解释说:“玄心可以说是超越感。晋人常说超越……超越是超过自我。超过自我,则可以无我真风流底人必须无我。无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以及死生,都不足以介其意。”超越二字,的确是玄心的真义。而中国文人之所以能有此玄心,则得益于玄学的滋养培育。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流,对魏晋文人来说,玄学不只是一套知识体系,更是一种内化于心,深刻影响他们立身行事的价值观念。玄学以《老》《庄》《易》为理论基础,强调以无为本,注重人的自然的、情感的一面。这就使玄学具有审美意味,与艺术深相契合。正如劳思光所言:“所谓'玄学’,基本上并非一严格系统。玄谈之士所取之精神方向,实是一观赏态度。在论'才性’、品评人物之时,固是以观赏为主,即就其议论形上问题或知识问题而言,亦仍是持此种态度。故魏晋玄谈之士谈'名理’时所重者在对此种'玄趣’之欣赏,并非真建立一种'学’。”这种“观赏态度”,即是审美态度,
极富审美意味的玄学,为魏晋文人赋予了“玄心”和“玄眼”,以此心与眼看待宇宙万物,便超越了世俗的功利考量,而附上了审美色彩。比如评论人物,不做政治性的考量,而是审美性的赏析。清谈论辩,不以理论追求为最终目的,清谈者的音声和辞采,探微析理的能力,你来我往的场面,足能娱心悦耳,使听者忘倦,沉醉其中。面对山水,不是求田问舍激起物欲的占有,亦不求仙问道,追求生命的延长,而是欣赏其佳美景致兴起濠濮间想,但得会心适意。日常饮酒,亦不以口腹享受为满足,而是追求人人自远、形神相亲、与清风明月为伴的诗意体验。欣赏书画音乐栖身山水园林,都意在营造一个超尘脱俗的审美世界。魏晋时期对于清远、虚、朗、畅、达等价值的推重,皆体现出玄学的超越性本质。以老庄为主体的玄学,加上深受庄学影响的禅宗,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塑造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
中国艺术所追求的趣味,即是“雅”的趣味,有此玄心与追求的人,便是“雅人”。蔡元培指出:“所谓雅者,谓志趣高尚,胸襟潇洒,则落笔自殊凡俗。”“雅人”必须具有高蹈的人格和高雅的趣味。因为文艺是对人性情的陶写,此种人格和趣味必然会投射于作品之中,因此,中国强调文如其人、书如其人、艺如其人,艺术理论中,首重人品。此一人品,固然带有儒家所注重的道德法则,如忠君爱国、光明正大。更重要的是,庄禅所培植的生命境界,要求人生的旷达、襟怀的坦荡、情感的真挚,即对世俗的超越,也就是中国文人所崇尚的林下之风、魏晋风流,
中国古代以文人为主体的艺术家,无论从事何种文艺创作,都追求此一人品,都需要有一颗超越之心,唯有如此,其作品才会脱俗不群。明代归有光在论文章体则时提到:“论古今人物风流,惟两晋为盛,故发之文章,神思自然飘逸。如陶渊明《归去来辞》,于举业虽不甚切,观其词义,潇洒夷旷,无一点风尘俗态,两晋文章,此其杰然者,苏子瞻二《赤壁赋》之趣,自此文脱出。”“潇酒夷旷,无一点风尘俗态”,便是超越世俗,带有纯然的审美性质,这既是陶渊明的人品,亦是他作品的精神境界,二者浑然无间。
在绘画领域,气韵生动是最高追求。宋代郭若虚指出:“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在郭若虚看来,历史上的绘画杰作,都是高人逸士所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品高洁,因其人品高洁,绘画的气韵自然高妙,生动传神。人品是成就绘画的必要条件。此类描述在艺术理论中比比皆是。明人唐志契在论述工笔画与写意画之别时指出:“夫工山水,始于画院俗子,故作细画,思以悦人之目而为之,及一幅工画虽成而自己之兴已索然。是以有山林逸趣者,多取写意山水,不取工致山水也。”唐志契处于南北宗之说盛行之时,高标文人画,贬抑院体画。在他看来,院体画乃“为人之画”,压抑了画家的兴味,缺乏画家的性情,文人画乃“为已之画”,旨在表达自己的“山林逸趣”。高旷的人品需要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就文人画而言,写意山水最为合适
明代文震亨精于造园与赏鉴,在他看来:“韵士所居,人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若使前堂养鸡牧豕,而后庭侈言浇花洗石,政不如凝尘满案环堵四壁,犹有一种萧寂气味耳。”所谓“韵士”,亦即高情远韵之士,也就是“雅人”,雅人的居住环境要与其人品相契合,必须和俗人的居所有分别,给人高雅绝俗的意味。朱厚爝认为琴有十四宜弹:“遇知音,逢可人对道士,处高堂,升楼阁,在宫观,登山阜,憩空谷,坐石上,游水湄居舟中,息林下,值二气清朗,当清风明月。”诸般场景,皆远离尘器令人有飘然高举之意。徐上瀛辨析了琴中的雅俗之别,他的观点很值得玩味:“但能体认得静、远、淡、逸四字,有正始风,斯俗情悉去,臻于大雅矣。”正始风,便是魏晋文人的超尘迈俗之风。清代黄图的《看山阁闲笔》中有一笑话,题为《闻琴》:“琴德最为高远不俗。有一善弹者,正弹之间,适村人担肥而至,闻声则肃然改容。弹者曰:'莫非知音者乎?’村人答曰:'某虽非知音,亦颇得趣耳。’”“村人”本为俗人,担肥听琴更是不雅,然他自谓能得琴中之趣,可见他亦有超越之心。
此外,在书画批评中,独标逸品,同样表明此点。唐代李嗣真将逸品置于其余九品之上,为最高等级。朱景玄在神、妙、能三品之外,提出逸品,宋代黄休复将逸品置于神品之上,作为对画作的最高评价,在他看来逸品具有“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的特点,就像写意画,逸笔草草,随意为之,不受规矩的限制,表达的是胸中逸趣,体现出心灵的自由。明代唐志契在论述逸品时指出:“惟逸之一字,最难分解。盖逸有清逸,有雅逸,有俊逸,有隐逸有沉逸。逸纵不同,从未有逸而浊、逸而俗、逸而模棱卑鄙者。以此想之则逸之变态尽矣。”总之,逸即不俗,超逸即高雅。
逸有自然之意,中国艺术同样以自然为最高境界。自然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本然状态,是天工,“大凡天地间,至微至妙,莫如化工。故曰神、曰化,皆由合于自然,不烦凑泊”。与之相对的,是人力,附着上了人为的痕迹,便显得造作,有违本然的面目。因此,文人艺术以自然为雅,追求自然而力避造作。
钟嵘认为颜延之的诗“错采镂金”,谢灵运的诗如“芙蓉出水”,自然可爱,这一风格为文人美学所崇尚。无独有偶,李东阳认为李商隐的诗缺乏自然之趣:“李长吉诗,字字句句欲传世,顾过于刿,无天真自然之趣。通篇读之,有山节藻棁而无梁栋,知其非大道也。”李诗如颜延之的诗,过于注重锤炼词句,而缺少了自然天成之趣。吕坤亦持类似见解,“诗辞要如哭笑,发乎情之不容已,则真切而有味。果真矣,不必较工拙。后世只要学诗辞,然工而失真,非诗辞之本意矣。故诗辞以情真切、语自然者为第一”。自然的情感发于本心,因此真切有味
书法同样贵在自然,“书贵质,不贵工;贵淡,不贵艳;贵自然,不贵作意。……自然,非信手放意之谓也,不事雕琢,神气浑全,险易同途繁简一致是已”。吕坤亦提到:“真字要如圣人燕居,危坐端庄而和气自在;草字要如圣人应物,进退存亡,辞受取予,变化不测,因事异施而不失其中。要之,同归于任其自然,不事造作。”书法与自然同工,不能显出雕琢的痕迹,唯有如此,才与大道相合
绘画亦求自然雅趣,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认为,宋代文人画“多求简易而取清逸,出于自然之性,无一点俗气”。印刻求雅,“故知雅者原非整饬,别是幽闲。即如美女,无意修容,而风度自然悦目,静有可观也,动亦有可观也,盖淡而不厌矣”。在周公谨看来,雅即不假修饰而自然可爱之意。他如园林,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为上乘。饮茶,以保持自然之清味为佳,如田艺蘅提出:“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更近自然,且断烟火气耳。”晒青者,保持了茶的自然之味,故受到推重。明清戏曲理论中,有“本色”之说。本色、真色,是与修饰辞章、填塞学问,使用靡词隐语等相对而言的,主张不假矫饰,自然流溢而出,反倒别具趣味。徐渭特别强调:“语入要紧处,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碓,不杂一毫糠衣,真本色。”王骥德亦指出戏曲当以“模写物情,体贴人理”为特点,“一涉藻缋,便蔽本来”,“须以俗为雅,而一语之出辄令人绝倒,乃妙”。为此,追求的是本色语和真情话。
以自然为雅、以逸为雅,皆有超越之意,此一意味的雅,清逸超俗温润恬淡,潇洒不拘。常以高雅、清雅、冲雅、淡雅、旷雅、和雅、温雅称之。在其背后,体现的是高洁的品格、才情和脱俗的趣味。
第三,以淡为雅。
《说文解字》释“淡”为“薄味也”。在五行的分类系统中,对应有五味:酸、甘、苦、辛、咸,淡虽不在其内,却被视为“五味之中也”老庄道家,将“道”视为最高的本体,道的特点,就是淡乎无味,无形无色,难以耳目等感官直接把握。“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因此,对“道”的把握,只能通过“收视反听”“坐忘”“心斋”来实现,通过虚而待物,保持一种虚静的精神状态,才能体验到“道”、把握到“道”。老庄对道的认知及其所主张的“全真”“守真”的人生理想,造就了一种素朴自然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此后,“淡”的追求,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美学4版权所有史和艺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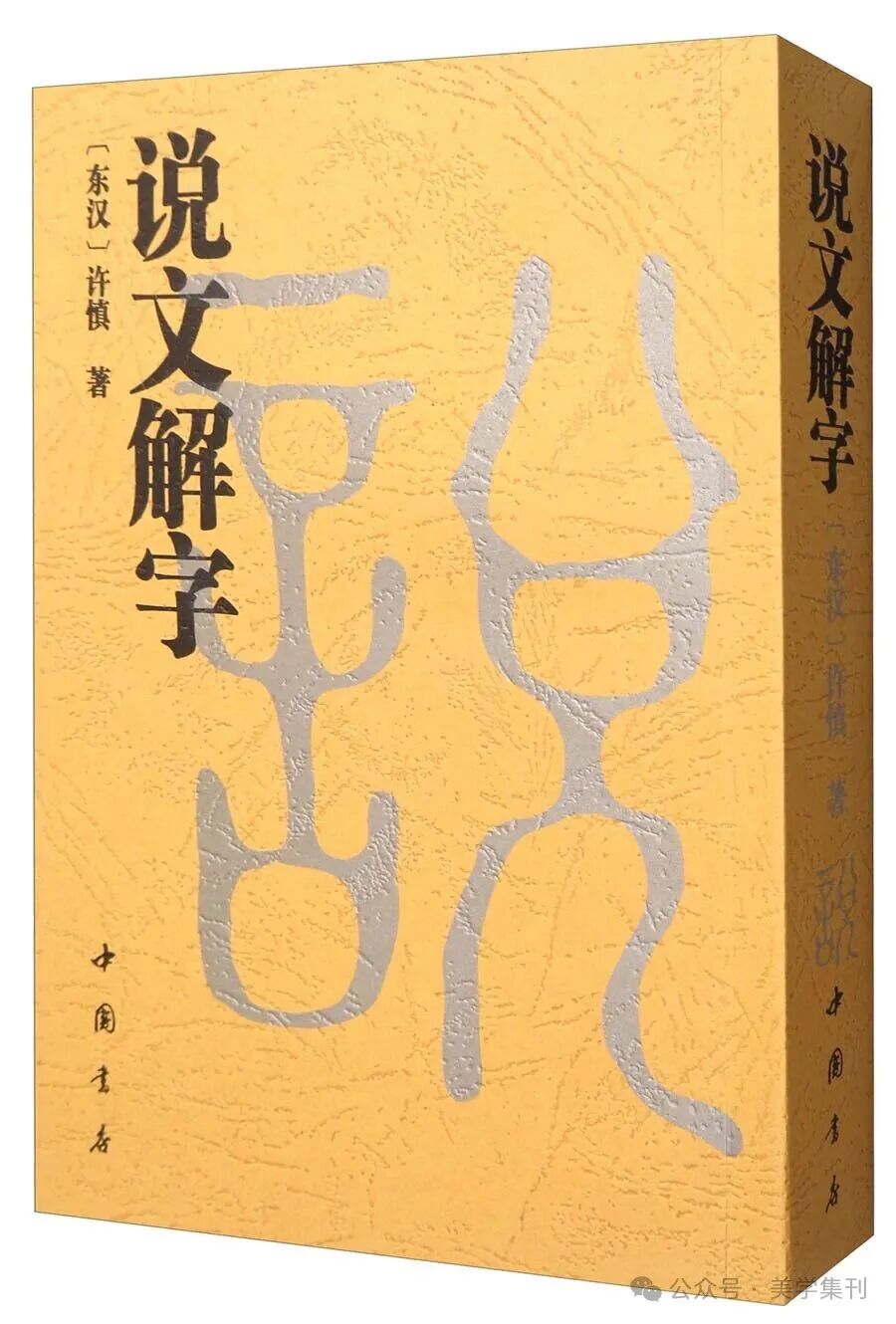
三国时期刘劭的《人物志》,是一部论人专书,在此书“九徵”篇中提到:“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材理”中又言:“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平淡”的气质禀赋,成为人物最高的审美特征。此一观念,显然受到了道家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成为主流思想,玄学即以老、庄、易为基干。文人的立身行事及文艺创作深受玄学影响,追求放达,希心玄远,追求超逸、自然的审美境界,此一境界,以“芙蓉出水”为代表,带有“淡”的特点。
中唐以后,禅宗兴起,强化了对“平淡”的追求。正如葛兆光所论:“禅宗是从印度禅学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内省反思方式及主张内心清净、生活淡泊以自我解脱的思想,促使了中国士大夫心理越加封闭、狭窄、脆弱性格越加内向克制,越加追求一种清净悠远的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越加忽视逻辑思维而偏向直觉思维。”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诸如冲淡(“饮之太和,独鹤与飞”)、沉着(“脱巾独步,时闻鸟声”)、典雅(“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自然(“幽人空山,过雨采苹”)、含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皆体现了对“淡”的追求。
宋代美学,更是如此。宋代的诗文、书法、绘画,无不追求平淡。如苏轼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欧阳修评梅尧臣之诗“以闲远古淡为意”。宋代书法,同样追求一种温和、淡泊的美感。宋代绘画,追求平远的境界。宋代的瓷器,同样体现出收敛、温厚、含蓄,朴素无华而蕴含独特的气韵,是一种自然平淡的美。可以说,平淡作为审美理想,贯穿于宋人的审美实践。明代美学之中,同样大量可见对于“淡”之趣味的偏好,此处略加征引。例如:
点铁成金者,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
书贵质,不贵工;贵淡,不贵艳;贵自然,不贵作意。质,非鄙拙之谓也,清庙明堂大雅斯在是已。淡,非浮易之谓也,大羹玄酒至味存焉是已。自然,非信手放意之谓也,不事雕琢,神气浑全,险易同途,繁简一致是已。
夫琴之元音,本自淡也。制之为操,其文情冲乎淡也。吾调之以淡,合乎古人,不必谐于众也。每山居深静,林木扶苏,清风入弦,绝去炎嚣,虚徐其韵,所出皆至音,所得皆真趣。不禁怡然吟赏……
世法惟恐不浓,出世法惟恐不淡。人惟淡故,其交恒:道惟淡故久而不厌。时习之悦,朋来之乐,不知之不愠,皆淡中滋味也。是故三世如来,究竟此“淡”者也;十方菩萨,分证此“淡”者也:声闻缘觉,得“淡”之一隅者也;老子庄子,窃“淡”之影响者也欲深入“淡”字法门,须将无始虚妄浓厚习气尽情放下,放至无可放处,淡性自得现前。淡性既现,三界津津有味境界,如嚼蜡矣。
茶自有真香,有真色,有真味。一经点染,便失其真。如水中着咸,茶中着料,碗中着果,皆失真也。
上述引文,博涉杂剧、书法、音乐、佛法、饮茶等领域,它们全都着意于“淡”的趣味和境界。淡,或与浓相对,或与真并提,指向的不是寡味和乏味,而是“似淡而实美”,是至味和至音,是活泼生动、神完气足的生命状态,直达“道”的真谛。欲得淡境,必须“将无始虚妄浓厚习气尽情放下”抛却世俗的欲望与成见,以虚静空灵的心境和状态面对生活,体悟大道。
第四,以拙朴为雅。
拙,《说文解字》释为“不巧也”,段玉裁注曰“不能为技巧也”,意指不擅手工技艺,粗笨拙劣,与工、巧相对。老子哲学主张绝圣去智,反对巧伪造作,提出“大巧若拙”“见素抱朴”。朴是道的本原状态,“先天道朴,无名无相”,在道家那里,“拙”和“朴”都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国文人讲究守拙、藏拙、存拙、抱朴,即为此一价值观之体现。
汉代美学推崇恢宏博大之气度,六朝美学尚“丽”,唐宋以后,拙朴的美学价值得到认肯,并将之作为一种审美追求,贯注于文艺领域。比如宋代陈师道于诗学领域主张“宁拙毋巧”,《漫叟诗话》中提出“诗中有拙句,不失为奇作”。王世贞倡导:“拙不露态,巧不露痕。宁近无远,宁朴无虚。”书法领域,宋代姜夔提出“与其工也宁拙,与其弱也宁劲,与其钝也宁速”,清代傅山亦云“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绘画亦求拙:“然则何取于生且拙?生则无莽气,故文,所为文人之笔也;拙则无作气,故雅,所为雅人深致也。”明代兴盛的印学更以拙为准则:“太作聪明,则伤巧;过守成规,则伤拙。须是巧以藏其拙拙以藏其巧,求所谓大巧若拙斯可矣!”“余见古印,虽一字不辨者,必印于简编,玩其苍拙,取以为法。”回沈野还将“拙”视为印法五要(苍拙、圆、劲、脱)之一。文震亨提到文房用具,“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
美学意义上的拙朴,绝非全无技巧的笨拙,而是一种高超的艺术表现,它抹除了人为和工巧,毫无斧凿之痕,显出妙造自然的艺术化境。如清代况周颐所说:“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纯任自然,不假锤炼。”因为纯任自然,不假人工,所以拙的境界是质朴的境界,内蕴着平淡而真切的情感拙与自然、真、质、朴、诚、古、厚等观念息息相关,体现出大道的真谛它摒弃了外在的浮华和人为的机巧,呈示着精神的解放和心灵的自由,体现出中国古人对于生命和自然的高度智慧和超然的审美态度。
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主编、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中国美学、艺术人类学。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美学集刊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