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姜坤鹏 徐云雪:女红文化的传承及其当代价值(一)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5-10-09 浏览量:1220
女红是从中国农耕文明中孕育出来的文化现象,是农耕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女红”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妇女手工艺品的制作技艺及其成品,与生活实用紧密相连,如刺绣、剪花、纺织、编织、缝纫、手绘、拼布、贴布绣等,均被称为“女红”。传统社会中,女红成品有衣、帽、鞋、云肩、肚兜、眉勒、荷包、挽袖、扇袋等,这些手工艺品的共同功能是服务日常生活与地方习俗。“女红”的第二层含义指从事“女红”工作的妇女,也可以称之为“工女”,或叫“红女”。据《考工记》记载:“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女红文化在多年的发展和传承过程中,形成了独特且深厚的底蕴与价值。从女红的发展演变来看,它既是日用之物,也是特定群体创造的审美产物,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往研究中,多数学者倾向于从艺术学、民俗学的角度考察女红文化,涉及物质的造型与装饰、女红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民间文化和生产活动。但女红不仅是一种审美文化产物,或者说不仅是中国古代造物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有着自身发展脉络,与各个时代相互融合且不断发展的有机体。因此,对女红文化进行研究就需要将女红与其所相关联的民间文化、日常生产生活相结合,阐发出中华民族文化中沉淀的集体意识以及无意识。当下的女红文化,正在经历着内部、外部的双重变革。研究女红文化的当代价值,要从当代文化语境中重新梳理、阐释其符号体系,发掘其在当代文化背景下所释放的活力以及魅力,重新审视其载体、功能以及在审美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对其价值进行拓展与重构。只有这样,才能对女红文化作出更深入更具前瞻性的探索,从而实现女红文化的活态传承。
(一)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
传统社会对女性从内在到外表、从举止到才艺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比如,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工”等几个方面作为选择妻子的标准,其中的“妇工”就是指女红。古代女子掌握的技能多为纺织、缝纫、刺绣等。《礼记·内则》中记载:“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女性从小就要学习刺绣、纺织、裁剪等女红技艺。掌握这些技艺是旧时女性的理想人格想象,也是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正因如此,女红文化在无形之中成为一种塑造中国传统女性理想人格的工具。
古代女性的活动多限制在家庭之中,女子的人格和社会角色也是在家庭中完成并实现的,家礼家训中关于女子的内容是了解女红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汉代班昭的《女诫》是早期较为系统地提倡女训妇教的书籍,全书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其中,将“妇功”提到妇德的高度加以论述:“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可以说,《女诫》是首次明确古代女性在传统伦理文化中地位和作用的理论表述,从文本上强化了女红的制度性功能。《女论语》由宋若莘、宋若昭姐妹于唐德宗时期撰写、注释,在流传过程中曾有失佚、增补,现存版本采用四言韵文叙述,简明易懂,易于在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民间妇女群体中传播。全文共十二章,包括“立身”“早起”“学作”“学礼”“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其中“学作”一章详细叙述了女红文化与技艺。“凡为女子,须学女工。纫麻缉苎,粗细不同。车机纺织,切勿匆匆。看蚕煮茧,晓夜相从。”这反映了古代女性对传统社会中“礼”的遵从,以及按照社会规范进行自我约束的心理状态。
在清代小说《红楼梦》中,“女红”与“女德”相表里,成为女教的核心内容,甚至成为“女德”的标志性符号。大户人家有“闺教”,普通人家也许会逊色一些,但也要求女孩心灵手巧,起码能动手做嫁妆和一些日用品。在古代社会,女孩子从六七岁就开始学习裁、缝、钩、织、编、绣、剪,这是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必修的“功课”。原因有三:第一,这是古代的道德观和文化审美对女性柔美气质的要求。第二,女红也是一种女子“竞技”项目,高超的技艺可以让女子在大家庭中获得地位。《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勇病补雀金裘”,讲的就是这类经典故事。晴雯因有一双夺天工的巧手,临危不辱使命,终化解危机。晴雯的织补技艺,奠定了她的“江湖”地位。第三,仕女们虽然基本没有经济生活压力,但是往往需要通过女红维持社交体面。《红楼梦》中体现出来的审美是有等级的,比如贾母就懂“软烟罗”,家世越尊贵,用的东西越要分得精细,修饰越要讲究。《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借描写贾母花厅里紫檀透雕上嵌的“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璎珞”,间接表现了出身于书香门第的苏州女子慧娘的高超绣艺。“《红楼梦》中的女红基本停留于劳动技能层面,即女红是‘技’而非‘艺’,是‘功’而非‘才’,因此,女红的笔墨、地位和审美价值在小说中不及诗文才艺。然而相对于其他文学作品对女红的弱化、简化、边缘化,曹雪芹还是忠实于生活的原貌,以大量、广泛的女红描写呈现了女性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⑨
总之,女红是塑造传统社会女性人格的主要途径,两千年来已经发展成为女教最为典型的形式、妇德非常重要的象征。“女红在中国的历史文化流变中淹没在以儒家主流文化观念为主导的世界外,从而转变为一门伦理的‘艺术’,一种‘三从四德’的实现工具。”⑩女红贯穿在传统社会女性的一生中,女儿、妻子、母亲的身份不论如何转换,“德、言、容、工”始终是传统社会要求女性必须具备的品德。
(二)女性自身诉求的体现
在传统社会中,女红文化虽受制于传统伦理的规训,却也以其独特的技艺体系成为女性表达自我诉求的渠道。女性通过纺纱、织布、刺绣、缝纫等工艺,将无形的精神世界凝练为有形的物质载体,部分作品以其技术之精微与审美之独到,超越了单纯的家庭劳动范畴,成为女性智慧与创造力的有力体现。在宋代流行的“缂丝”技艺,就以其“通经断纬”的方法织成繁复的图案,其工艺要求分毫不差的经纬计算与合宜的色彩搭配。女性匠人在此过程中,既展现了数学思维的严谨性,又以花鸟、山水等意象暗藏对自由的向往。这种技术实践不仅是生存技能的体现,更成为女性自我价值的有力证明。
女红技艺的传承蕴含着女性群体的技术革新意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流行的“闺阁绣”,是一种由女性创造的“劈丝如发”的极致工艺。绣娘们通过将一根蚕丝劈分成十六股细线,以针代笔绣制名家的书画作品,在方寸绢帛间重构文人意境。这既是对文人艺术的再现,亦是对自身艺术造诣的证明。女性在日复一日的穿针引线中,不仅磨砺出超乎寻常的耐心与专注力,更通过纹样设计、配色法则等个性化的创造,将在社会规训下的“妇功”升华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语言。
技术的掌握还赋予女性有限的经济自主权。在“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中,虽然“女织”常常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女性纺织品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经济收入。蜀锦织造中的“挑花结本”技术,要求织女记忆数百种提花程序,通过错综复杂的经纬交织塑造立体纹样;闽南地区的“金苍绣”以金银线盘绕出浮雕效果,其作品常作为贡品进入宫廷。这些高附加值的工艺使得女性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贡献者,技艺精湛者甚至被尊为“国手”“针神”等,社会地位虽未突破性别框架,却能通过技术权威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尊重和话语权。
更深层的诉求体现在文化符号的编码中。女红作品中的石榴、莲花、蝴蝶等纹样,既是吉祥寓意的表征,也是女性生命经验的隐喻。苗族女性将族群迁徙史转化为服饰上的几何符号,客家女性用“缠枝纹”暗示对宗族绵延的期许,这些通过针线书写的“无字史书”,实则是女性对历史叙事的另类参与。此外,女性所绣的荷包、鞋垫、绣球等物品有的是定情时的信物,有的是结婚时的用品,其上的装饰表达了她们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旧时的社会环境令她们无法将自己的情感宣之于口,所以她们选择采用婉约、含蓄、象征的手法,通过女红制作来宣泄她们内心深处复杂的情感。
因此,女红的制作实为女性在礼教夹缝中构建的主体性表达。她们以针为笔,以线为墨,将社会规训转化为技艺修炼的道场,在经纬交错之间,既恪守着“妇功”的本分,又悄然书写着超越时代的自我证言。这种矛盾而统一的技术美学,最终使女红超越了实用主义的范畴,成为传统社会女性实现精神自洽的独特路径。
传统手工艺的审美特质体现为“工”与“意”的统一:一方面,技艺的精细程度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如苏绣中的“平、齐、细、密、匀、顺、和、光”八字诀,既是对工艺的规范,也体现了制作者对于美的极致追求;另一方面,纹样和色彩的选择承载着女性审美共同的象征系统,比如龙凤象征祥瑞,石榴隐喻多子等,这些符号通过代际传承形成稳定的审美范式。传统女红的审美始终依附于实用功能,其价值因时代的局限性被框定在“妇德”与“日用”的范畴之中,未能脱离家庭伦理与物质需求的限制。
但是,当代女红文化的审美打破了这一传统逻辑。国家大力支持非遗保护工作为女红提供了从“生活技艺”向“文化遗产”转型的契机。在非遗视角下,女红的审美价值不再局限于其实用性,而是被重新定义为“活态文化基因”的载体。例如,苏绣、湘绣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通过博物馆展览、国际艺术交流等途径,将传统的针法转化为纯粹的艺术语言,刺绣的“双面异色”“虚实乱针”等技法被解构为视觉实验的媒介。这种转向的核心在于,女红从“技艺的工具性”升华为“主体性的表达”——艺术家以针线为笔,将个人对性别、生态、记忆等议题的思考融入创作。比如,梁雪芳创作的《荷韵》系列(图1),以水墨意境重构苏绣,用丝线的光泽模拟水波的流动,使传统工艺成为当代艺术的叙事工具。

▲ 图1 梁雪芳刺绣作品《荷韵》(梁雪芳 提供,2010年)
当代审美的“破界”特质,进一步凸显了当代女红与传统女红的差异。数字技术的介入让当代女红突破了物理材料的限制。3D打印刺绣、LED光纤织物等创新形式,将传统纹样转化为动态光影艺术,并且为女红制作带来了材料上的革新。
与此同时,女红的审美价值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可以被重新诠释(图2)。更深层次的审美转型,源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当代女红不再是被规训的“闺阁艺术”,而是展现女性话语权的文化实践。艺术家尹秀珍以旧衣物为材料编织巨型装置,将缝纫行为转化为对消费主义与女性劳动的批判;同样,艺术家林天苗耗时五六年完成的刺绣地毯《妳!》,是将从《康熙字典》到当代网络媒体中精选的描述女性的词汇,用针线“书写”的女性身份标签变迁史。这些词汇既有“贤淑”“贞烈”等传统规训,也包含“独立”“酷儿”等现代宣言,甚至捕捉到了短暂流行的网络俚语。艺术家在针线间完成语义更迭,使女性从“被定义”走向“自我命名”。这些创作颠覆了传统女红“温顺”“私密”的刻板印象,赋予其新的美学力量。在此过程中,女红的审美价值与女性身份认同形成共振——制作女红既是连接代际记忆的纽带,也是重构性别叙事的利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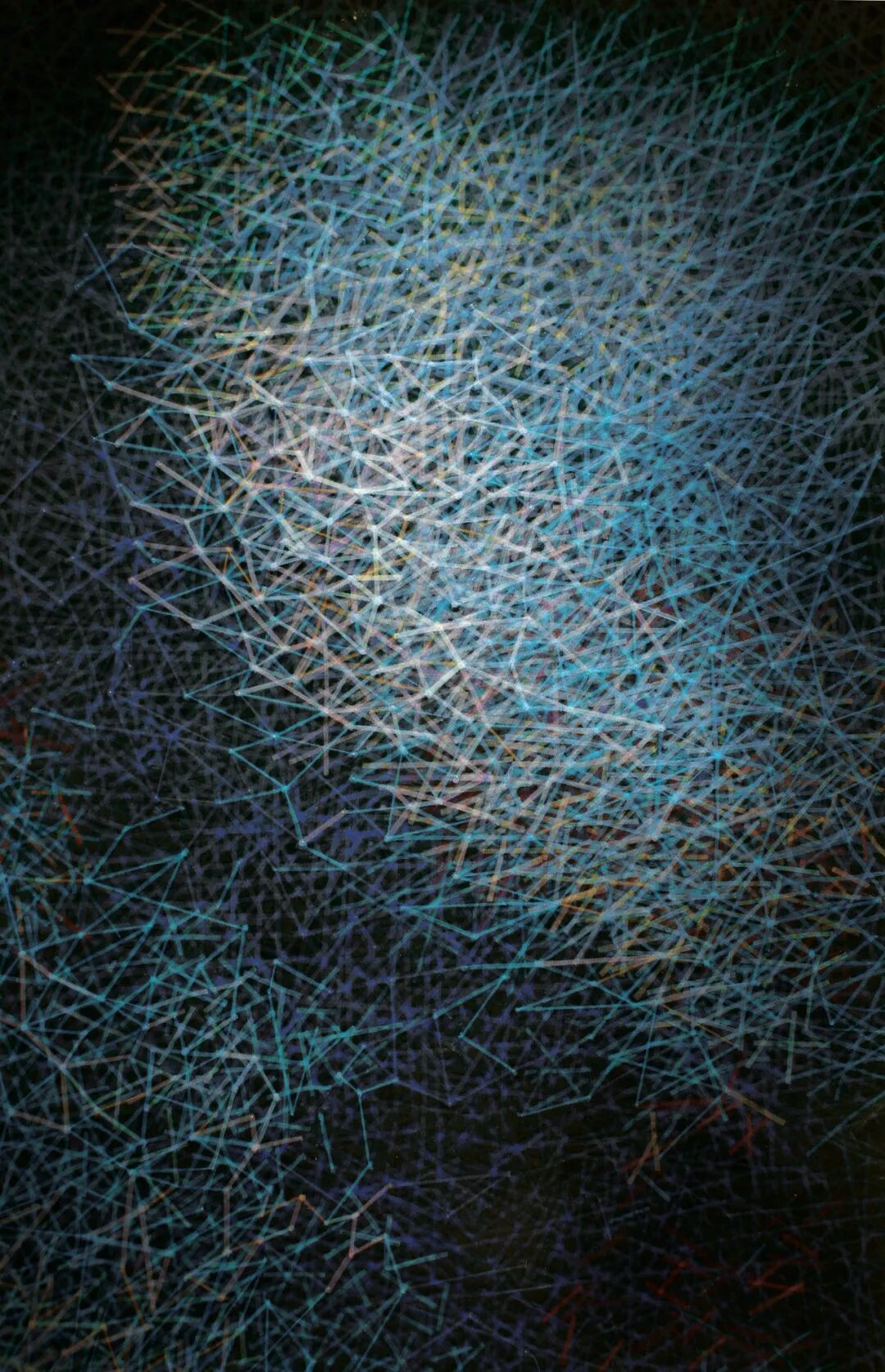
▲ 图2 岳嵩纤维艺术作品《你和我》(岳嵩 提供,2012年)
总之,当代女红不再追求“完美复刻”的传统,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将女红置于现代艺术和技术哲学的交叉点。这一转型不仅让“女红”这种古老的技艺焕发新生,更使其成为反思现代性危机的一种美学方案。手工艺的“不完美”与“人性温度”恰恰弥补了机械复制时代带给人的“重复感”和“冷漠感”,当代女红文化的价值亦在于此。
作者简介:姜坤鹏,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手工艺理论与设计史论;徐云雪,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