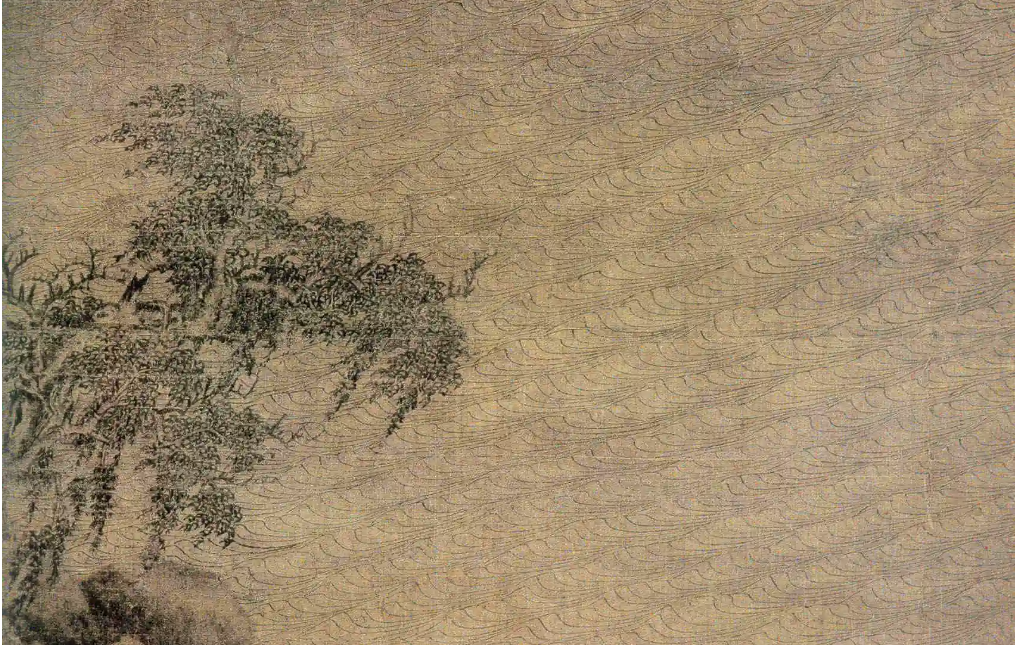在20世纪40年代“是汉学还是艺术史”的大讨论之后,欧美汉学界针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出现了不同于“艺术汉学”收藏品鉴阶段的三个特征:一是“汉学家”和“艺术史家”逐渐实现身份合流,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学者群;二是传统汉学的考据方法和艺术史的风格分析法在论证中互为补充;三是在译介更多艺术理论文献的基础上,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艺术”有了更明确的规定性,也寻回了在“艺术汉学”阶段被遮蔽的研究疆域。20世纪中叶,“新艺术汉学”应势而生,集中表现在学科意识的自觉和多元的学科形态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汉学界更新了“范式”,以跨文化和跨学科为表征的“新艺术汉学”进入了元学科甚至后学科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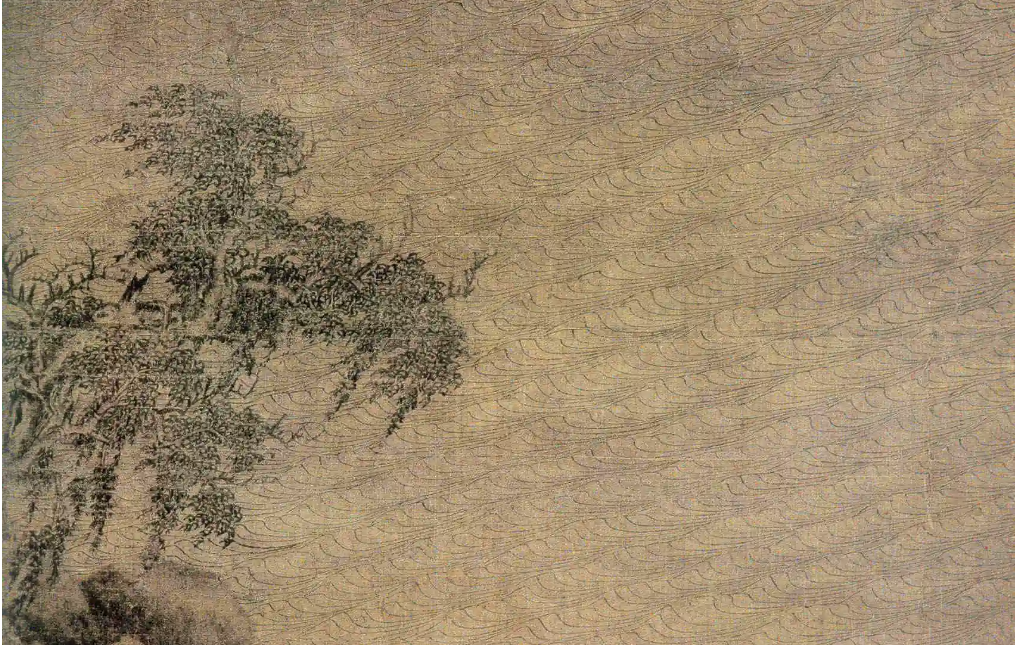
20世纪40年代,欧美汉学界掀起了“是汉学还是艺术史”的论争,引起了“图像—风格”和传统汉学两种研究方法的分歧以及“汉学家”和“艺术史家”两大学者阵营的对垒。虽然这场大讨论在之后欧美汉学界关于“范式”的探索中终结,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需要反思:首先,“汉学”作为域外(海外)关于中国的学问,“中国艺术”是其中的一个分支,“汉学”派和“艺术史”派的论争为何会产生?其次,20世纪初以收藏和品鉴为基础的“艺术汉学”形成,除了瓷器、绘画、造像等“美术”或称“视觉艺术”以外,何以音乐、戏曲等门类不在其中,书法也时隐时现?再次,大讨论以后,如果说欧美汉学界在“中国艺术”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上达成新的共识,在学者群、学术研究上发展出新的格局,那么是否意味着在“艺术汉学”之后,新的阶段已经到来、新的学科形态正在发展?“新艺术汉学”是否已然来临?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讨论。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兴起的、以中国艺术品收藏和品鉴为基础的“艺术汉学”,可以说是继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以后,在专业汉学阶段,全面、集中地关注“中国艺术”的开端,对欧美汉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艺术汉学”将“中国艺术”锁在了“美术”(或称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的范围之内,包括了园林、雕塑、工艺美术、文人绘画和书法等,同时期欧美汉学界对中国音乐、戏曲、舞蹈等艺术门类的涉猎也从未缺席,只是散落于其他汉学领域之中。换言之,“艺术汉学”使美术和其他艺术门类在欧美汉学的现实格局中分道扬镳,但在学科发展形态上,“中国艺术”是以多门类作为汉学研究对象的,被称为“艺术史”的研究在实际上被美术史研究所取代。与其他门类相比,美术研究更集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欧美汉学界在20世纪40年代掀起了“是汉学还是艺术史”的大讨论。“汉学家”和“艺术史家”被看成是研究“中国艺术”的两大阵营,而主要分歧则在于“图像—风格”分析法和传统汉学方法在面对中国“视觉艺术”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问题。大讨论后,欧美研究“中国艺术”的学科样态出现了三个表征,宣告着“新艺术汉学”阶段的到来。第一,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学者群。“艺术汉学”使一批欧美收藏家转变为汉学家,而在大讨论中,原本泾渭分明的被称为“汉学家”和“艺术史家”的学者也在观点和方法的碰撞中“合流”,关注“中国艺术”的汉学家形成了一个整体。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凝聚共识,探索行之有效的“范式”。大讨论的焦点并不在于研究对象,而是“图像—风格”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和重考据、重文献的传统汉学研究方法之间的交锋。在两种研究方法的争胜局面终结后,研究“范式”在更为多元和开放的学术视野中生成。第三,明确的研究对象形成一定的规定性。“艺术汉学”使更多中国“视觉艺术”被纳入研究对象之中,种类更为齐全。大讨论之后,“汉学派”将画论、书论、诗论等中国古代艺术理论文献作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音乐、戏曲及其相关的理论文献也出现在了欧美汉学家的研究范围之内。由此可见,如果说“艺术汉学”是欧美“新艺术汉学”的基础性准备阶段,那么大讨论无疑是欧美“新艺术汉学”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上述三个表征在大讨论阶段究竟是如何逐渐显现的呢?1935年,德国学者巴赫霍夫(Ludwig Bachhofer)在《公元8世纪的中国山水画》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目前关于唐代绘画的研究材料,有很大一部分源于一种落后的方法论:落款、题跋、印章、笔记等文本,不足为信,不足为据,我认为这样的路径应当被抛弃”。他批驳了传统汉学的考据方法,强调从风格着手,划定了“汉学”和“艺术史”方法论的边界。1947年,美国古董商人、陶瓷收藏家、学者波普(John A.Pope)发表了《汉学还是艺术史——中国艺术研究方法笔记》,开宗明义地谈到,艺术史家用他们熟悉的视觉感知方式把握绘画、造像、建筑、瓷器等艺术作品的物质材料和媒介,用训练有素的图像分析和风格演变方法进行分期、断代,而汉学家在艺术人类学考察中对文献、文本和文字的重视或许可以弥补艺术史家在治学方法上的不足。他将关注“中国艺术”的学者划分为“汉学家”和“艺术史家”两个阵营,并批评了作为“艺术史家”身份的巴赫霍夫在《中国艺术简史》中的“图像—风格”研究,指出其不熟悉中文所导致的缺陷。1953年,巴赫霍夫的弟子罗樾(Max Loehr)在《安阳时期(1300—1028B.C.)的青铜器风格》一文中批评了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青铜器纹饰三分法。他指出,“高本汉的三分法系统依赖于‘写实性饕餮纹’的先验概念,这并没有提供历史风格延续性变迁的逻辑解释。这个系统是静态的”。罗樾反对高本汉未经考古学证实的文献统计,在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的基础上,运用风格史类型分析的方法重新划分了青铜器的周期序列。“罗樾对殷式青铜器的卓越研究,为长期受到贬抑的风格分析赢得了应有的声誉和地位,同时也极大地激励了后来的艺术史学者将风格分析引入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信心。”事实上,罗樾的风格类型分析建立在考古学文献的基础上,这相比之前“艺术史家”的方法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尽管他仍未脱离“图像—风格”的框架,但减少了先验色彩和思维定式,增强了实证性。在“汉学”和“艺术史”激烈交锋的时期,瑞典学者喜龙仁(Osvald Sirén)试图将“汉学家”的文献考据和“艺术史家”的实证分析结合起来。1949年,他出版《中国园林》一书,在描述和总结自己来华考察园林经历的同时,引用了《十竹斋书画谱》《芥子园画传》《园冶》《红楼梦》等文献和多处园林的绘画图记、诗文典籍。“此时西方学者对中国园林的解读开始建立在一手的中国文学资料基础之上,逐渐打破此前‘西方透镜’之下凭空而论的桎梏。”喜龙仁的园林研究既包含了“图像—风格”分析,又阐释了中国古代画论、园林理论,同时根据论述场景的需要引用古诗词,成功调和了“汉学家”和“艺术史家”的身份冲突。事实上,早在1936年,喜龙仁就出版了《中国画论》,编选和译介了汉代至清代的画论,附录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书目,选录超过70幅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以宋代画论这一部分为例,喜龙仁不仅阐述了苏轼“诗画合一”的艺术思想,还结合具体的绘画和诗歌作品进行论证。喜龙仁这种试图消除“汉学”和“艺术史”方法论隔阂的努力贯穿大讨论前后。尽管他在20世纪中叶提出并倡导这种能够互补的研究“范式”,但在当时并没有能够真正统一两大阵营。然而,喜龙仁的身体力行和大讨论的思想洗礼使“汉学”和“艺术史”愈发在学者群中获得了学术观点的一致性,并在方法论上达成共识。在此之后,无论是早期关注“中国艺术”的夏德(Friedrich Hirth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还是“二战”后崭露头角的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韦陀(Roderick Whitfield),他们都被认为是研究“中国艺术”的汉学家。至此,欧美“新艺术汉学”学者群的发展已渐趋成熟。20世纪60—80年代,尽管关于“中国艺术”的各种研究仍不可避免带有大讨论时期的基本方法偏向,但均承认单一的“图像—风格”分析和孤立的文献求证都存在方法论上的先天不足。“汉学”和“艺术史”的方法不再彼此对立,而是融合、互补的关系。作为新兴的合并了艺术史家身份的汉学家,“新艺术汉学”方法论的自觉也体现在更多的中国古代艺术理论文献成研究对象,不再仅作为艺术史的旁证或补充。1961年,高居翰(James F.Cahill)发表《谢赫“六法”的解读》回应威廉·埃克(William Acker)对“六法”的新诠释。“关于‘六法’第三条和第四条的新解为曾经简单、直白的译介注入了更丰富的含义,但‘六法’的多义性也正是其本质特征,从而引发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继承性研究。”在此文中,高居翰借助《四体书势》《草书状》《叙画》等文献对“六法”进行评述,强调了理论文献对通达“中国艺术”要义的必要性。方闻(Fong C.Wen)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结构分析”以后,越发关注“中国艺术”的整体情境,探寻“形式”和“观念”的关系问题。在他和姜斐德(Alfreda Murck)于1991年共同主编的《文本与图像》序言中,中国古代诗书画一体的现象被认为是“诗学理论”“两宋院体画”和“诗入画”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可以说,观念、技法、体制,都被置入“形式”,或曰由“形式”得以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讨论时期学者身份和方法论的“和解”在欧美“新艺术汉学”阶段表现在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中国艺术”的规定性延伸和范围拓展。卜寿姗(Susan Bush)在1971年出版的《中国文人画:从苏轼到董其昌》(中译本名为《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中对宋元明诗书画论和题画诗、题跋等文献运用自如。她在1981年发表的《金代的考古学遗存(1115—1234)》一文中在方腾(Jan Fontein)和吴同(Wu Tung)的研究基础上对位于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金代遗址的发掘成果和金代佛教艺术、陶器、绘画和书法的文献进行了整合。从卜寿姗这种继承性、综合性的研究特征来看,欧美汉学界“新艺术汉学”的学者身份、方法论和研究对象这三个表征均显示了较为成熟的学科发展境况。二、寻回欧美“中国艺术”研究在“艺术汉学”阶段被遮蔽的疆域如果说“新艺术汉学”是“艺术汉学”的进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规模和影响也更大,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集中体现在上述三个表征,那么“新艺术汉学”对“艺术汉学”的超越首先表现在克服了“艺术汉学”因始于艺术品的收藏和品鉴而更多关注“美术”(或称“视觉艺术”“造型艺术”)的局限;其次,“艺术汉学”对画论、书论、诗论的运用往往是美术史研究的辅助,而“新艺术汉学”则打破了“史”和“论”的偏重关系;再次,“艺术汉学”将《礼记》《庄子》《沧浪诗话》《传习录》《原诗》等看作艺术“外围”的哲学文献或文学文献,而“新艺术汉学”则将其看作能够更好理解“中国艺术”的基础文献。换言之,大讨论从思想和现实上均使欧美的汉学研究从“艺术汉学”过渡到“新艺术汉学”阶段。然而问题在于,“中国艺术”对于欧美汉学界而言是一个建构的概念。我们对“艺术汉学”阶段的认知通常不包含关于音乐和戏曲的研究,并不意味着相关的研究就是缺位的。相似的情况还有,书法作品(包括绘画的题跋、印章和碑刻拓片等)原本就是“艺术汉学”阶段欧美众多收藏家和博物馆的藏品,但“书法”曾一度处于汉学研究隐而不显的领域,这也并不意味着书法不属于“中国艺术”。正如柯律格(Craig Clunas)所言:“‘中国艺术’是新创造的词汇,它出现的时间不足百年……尽管中国有漫长而富有经验的书写艺术的传统,世世代代贵族文人爱好收藏、陈列以及消费艺术品,但是在19世纪以前,无人将这些物品视为同一领域的组成部分。”因此,“新艺术汉学”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欧美汉学界对中国音乐、戏曲、书法等种类进行研究的突然“降落”,而是在“艺术汉学”阶段被遮蔽的疆域被寻回、照亮。这些曾经隐藏而从未缺席的研究领域在新的阶段被统合到了“中国艺术”的研究中,重新登场。书法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功能性的书写行为,在欧美汉学界的早期研究中,没有获得充分的关注。除了1919年福开森(John C.Ferguson)在《中国艺术史大纲》中明确列出书法类别以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书法却极少受到欧美汉学界的关注。在“艺术汉学”时期,书法类的藏品并不是主流,也造成了这种遮蔽的延续。大讨论以后,魏礼泽(William Willetts)、普罗丹(Mario Prodan)、阿巴特(Francesco Abatte)、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华威廉(William Watson)、特里吉尔(Mary Tregear)等均在著作中专门对书法进行叙述。“汉学”和“艺术史”的合流提高了欧美汉学界对中国汉字,尤其是汉字书写作为美的艺术的重视程度,同时学者们也渐渐从“他者”视野的桎梏中走向还原整体情境的“中国艺术”,尊重中国文化传统。“新艺术汉学”的到来,也正是书法在欧美汉学界获得学科意义上“合法”资格的时刻。利特尔(Stephen Little)于1987年发文指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书法都被认为是远东最高级的艺术形式,但在西方被广泛接受却是很晚近的事……大量的书法作品以诗歌或散文题字出现在绘画作品上,或是以长篇目录、扉页的形式存在。”在利特尔看来,文本的意义层面和视觉的抽象形式层面对于书法的价值而言,是缺一不可的。他进而认为:“书法家对章法、字法、笔法的注意是技艺水平和心理状态的反映,也是接近和追求自然的无阻滞力量的意义表达。”将书法看成是一种复杂的书写行为,关注其视觉艺术性、社会性、文化载体性等侧面,这样的观察方式逐渐获得认可。倪雅梅(Amy McNair)提出:“书法和正字法在唐初(618—907)是评估道德素养的重要手段,即如‘字如其人’的中国传统观念。书法表达的公共话语和价值观作为唐朝科举制度的要求,是否得到了践行?抑或只是得到了文人在书法批评和鉴赏时的拥护?”这种认识将书法看成是政治伦理符号,而不仅仅是美术史的一个特殊类型或绘画的附属“文本”,更接近书法在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中的底色。至此,书法在欧美汉学从被遮蔽到被照亮,从美术史的特定类别到“中国艺术”的有机组成,构成了“新艺术汉学”的重要疆域。在“艺术汉学”阶段,也有学者将视线挪移到“美术”以外的门类。1889年,沙畹(Edouard Chavannes)运用《淮南子》《史记》《吕氏春秋》《左传》等文献作为佐证,将构成中国律学之基石的三分损益法的起源归结到古希腊。20世纪以后,音乐研究逐渐从汉学对于经史子集的研究中分离出来,涌现了库朗(Maurice Courant)《中国古典音乐史论》(1912年)、拉卢瓦(Louis Laloy)《淮南子与音乐》(1914年)、耒维思(John Hazedel Levis)《中国古代的音乐艺术》(1935年)等成果。这些著述虽然构成了欧美汉学界研究“中国艺术”的一部分,但人们对“艺术汉学”的认知通常并不包含此类研究。语言习惯和学科发展的指向性造成了音乐成为“艺术汉学”阶段被遮蔽的研究疆域。在同一时期,葛兰言(Marcel Granet)分别于1919年和1926年出版了《古代中国的祭日和歌谣》以及《古代中国的舞蹈和传说》。前者探讨的是“平民婚俗”,后者“揭示了先秦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宗教思想的演进”。尽管他在研究中大量引述《诗经》和《礼记》,但对音乐和舞蹈的关注更多是为了“展示先民遗风演进和贵族礼制的历史过程”以及“分析君王权威如何得以建立”。换言之,在葛兰言的音乐和舞蹈研究中,并未有意识地将视点凝聚在“中国艺术”之上。可见,学科意识的自觉和学科归属也成关于音乐、舞蹈等门类的研究失落在被隐匿、被遮蔽疆域的原因所在。大讨论后,在学者群、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上更具有整体性和规定性的“新艺术汉学”初步形成,音乐、舞蹈、戏曲等门类的研究摆脱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在学科归属上含混不清的境遇。钟思第(Stephen Jones)在《源与流:中国早期音乐与生活传统》中说:“从生活传统的观念来认识音乐,是包含历史主义视角的。历史源流的丰富性决定了中国音乐并不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将早期音乐和古典音乐从生活传统中割裂开来是不可取的。”在他的研究中,人类学的方法和文献学的方法相互补充,但研究的第一对象是音乐而不是民俗或伦理等制约因素,这几乎毫无争议。正如钟思第会被认为是关注中国音乐的汉学家而不是以音乐为研究工具的历史学家或民俗学家。此外,依维德(Wilt L.Idema)与韦斯林(Stephen H.West)合著的《1100—1450年中国戏剧资料集》收录了《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文人笔记,突破了以杂剧文本为中心的程式,描绘了戏班组织结构、剧本生产、演员社会地位和演剧空间的社会图景。他们借助社会学的方法所聚焦的研究对象,与其说是文学或戏曲文学,倒不如说是戏曲或戏曲艺术。埃里克(Eric P.Henry)的《中国人的娱乐:李渔的戏剧》对《闲情偶寄》的部分章节和“立主脑”等概念进行了译介和阐释。他在文末指出:“李渔既属于滋养他的深沉而敏锐的中华文明,也属于世界文明的共同体,就像我们的阿里斯托芬、乔叟和莫里哀。”埃里克花了大量篇幅试图从观众的视角解读所涉四部作品的情节、结构和效果,并且带有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色彩,使其研究的学科归属逾越了文学的范围,更靠近戏剧本身。 葛融(Levi S.Gibbs)在《中国表演艺术传统的面貌》一文中提出:“用一种中立的观点看待中国表演艺术的‘持续’与‘变迁’,而不是关注话语霸权或创造性演变。”从学科形态来看,此类研究通常将中国传统的戏曲、曲艺、舞蹈表演视为一个整体,看待为人类表演活动或行为的“中国艺术”。1969年,美国创办了《中国演唱文艺》期刊,将口头表演的“中国艺术”划为一类,囊括了戏曲、曲艺、民歌甚至诗歌、谚语、小说、散文等。学科意识的自觉、新的学科形态和新的学术研究均表明,在“艺术汉学”阶段被遮蔽的研究疆域,在“新艺术汉学”时期已渐渐显现。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研究杂志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