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专业委员会 > 工作动态
理论 | 赵谦:商业与艺术的合力——“中国伊万里”瓷装饰探究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3-04-24 浏览量:1637
1. 对日式装饰的模仿与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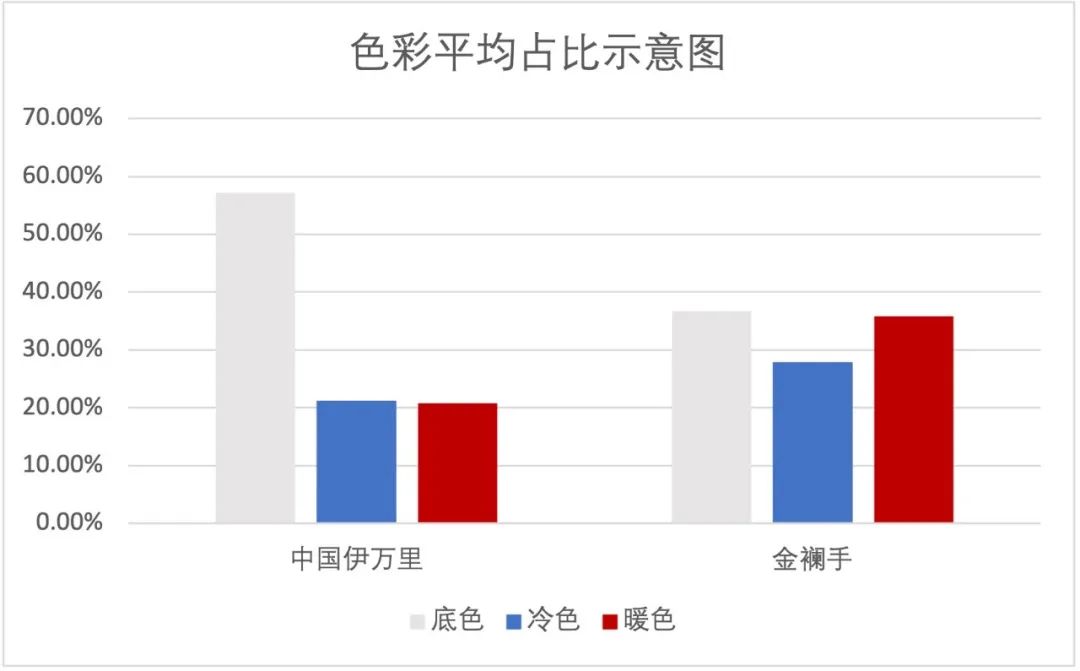
2. 西来纹样的融合


二、装饰标准化:图案中的程式与模件
1. 花卉造型的程式



2. 构图中的程式






3. 模件化的图案构成




1. 画谱中的模件




2. 行业分工

3. 利益与潮流
(1)利润和风险
(2)成套餐具的流行
2022首届物质文化与设计研究青年学者优秀论文评议
第一组 工艺美术史研究 三等奖,作者简介:赵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专委会公众号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