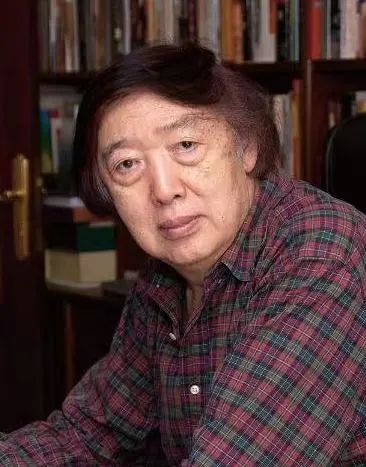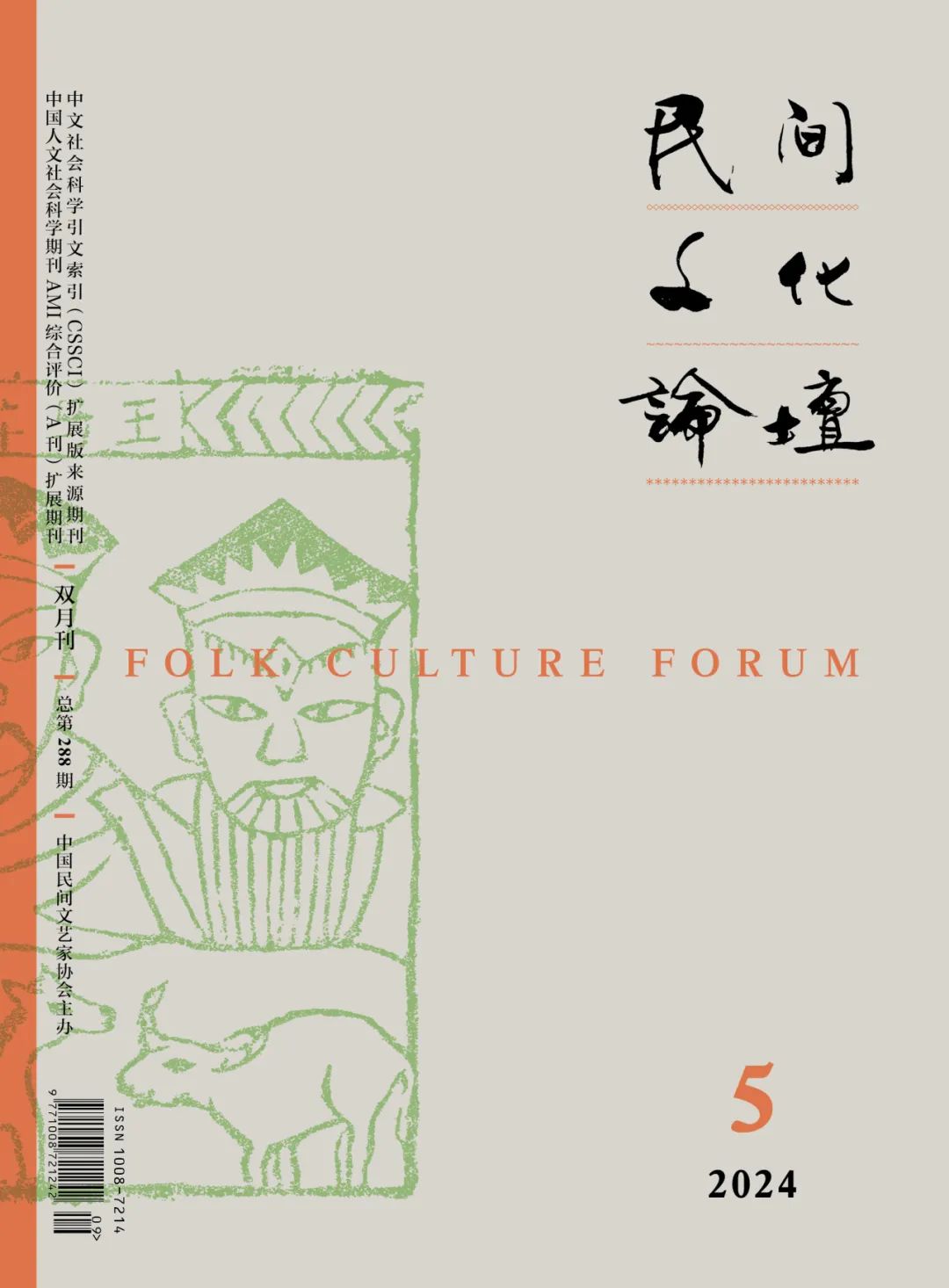自眹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年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民间文化正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非遗”)的名称进入人类文化保护的视野。20多年来,中国非遗保护从普查入手摸清家底到形成四级保护名录,构建了多样化保护模式,进入科学保护阶段。随着非遗学科的建立,非遗从“保护实践”逐步向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转向。然而非遗保护过程中仍存在大量传统文化衰微乃至消失的问题,民众对非遗的审美价值认识不足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民间文化这种粗朴稚拙的草根艺术究竟美不美?作为活态的非遗审美文化有何特殊的美学价值?文章通过对中国非遗研究专家、“ 民间文化保护第一人”冯骥才关于非遗之美的体验、品藻和鉴赏的访谈,为我们看待非遗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刘明明(以下简称“刘”):先生好!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今天想听先生谈谈“非遗之美”。美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但是我们怎么能看见、发现、感知它?您认为“美”是什么?冯骥才(以下简称“冯”):我同意柏拉图对美的经典解释,柏拉图认为真、善、美就是美的极致,当年我写“挚爱真善美”的时候就想到了柏拉图;我也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另外一种解释,认为“美就是生活”,美在生活中无所不在。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美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客观是美,主观是审美,我用我的眼光来体验、感受或者接受、判断、确认了这个美,这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人为什么能够体验美、感受美,感知判断甚至能够创造美?我认为美是一种人性。人性本身就是能够感知美,原始人就能够感知美。他能知道陶罐那么做美一点,最后马家窑的罐都那么做,为什么不是这么一个形而是那么一个形?画家孙奇峰跟我说,“一个瓶子最重要的是两条轮廓线”,这个轮廓线是当地的人用一两千年锤炼出来的。比如邯郸的罐子,属于燕赵之地,是通透饱满两条鼓起来的线,那个地方人认为这种线就是美的;江南认为梅瓶美 , 一种细高美,地域气质都表现在它轮廓的美上了。美的东西,为什么大家都认为美,因为每个人都有美的基本的人性,所以美是人本身带来的。这是我的理解,是我对美的一个哲学理念。当然因为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教养的原因,美有高下的区别。刘:“非遗美学”是不同于西方经典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的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学界还没有成熟的非遗美学理论。我想请教先生,您认为什么是“非遗美学”?冯:我以前在讲话或者文章里边从来没有提过“非遗美学”这个概念, 能不能用“非遗美学”这个概念?我犹豫。因为犹豫,所以我没有提过,我只提过“非遗的美学价值”,非遗毫无疑问是有美学价值的, 而且非遗的美学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非遗有五个价值。第一个是非遗的“历史价值”,因为它是“遗产”,有一个历史的漫长的过程,所以它一定是有历史价值的,这是第一个价值;第二个价值是它的“文化价值”,它有文化内涵,比如它包含这个地方的信仰,包含这个地方人和自然的关系, 包括这个地方独特的民族历史, 这些东西都是它的文化内涵,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是它的“地域价值”,比如海南的非遗, 黎族的习俗一定有它独特的地域价值;第四个价值是它的“遗产价值”,它能成为遗产, 而其他很多民间文化是不能成为遗产的, 所以非遗很重要的一个价值是它的遗产价值;第五个价值是它的“美学价值”,不见得只有艺术才有美学价值,不是艺术也有美学价值。它只要成为遗产,就有美学价值。比如一个习俗,它并不是作为艺术,作为一个舞蹈、戏剧或者美术,它就是一个习俗也有美学的价值。看起来也有一种美,非常独特的美。所以我说非遗有它的五个价值。而且每个价值里边都有美。比如地域价值,我们讲非遗的地域性,地域性也是一种“地域美”,也是一种地域的美。天津人老城里过年的时候, 有一种独特的地域的美, 你要是有文化学者的眼光就能观察出来,它是独特的一种美。它是历史的,它有一种“历史美”。我们说一个历史建筑,这个历史建筑迷住你的不是它的造型怎么独特,它迷住你的首先是一种“历史美”。历史气质是一种文化的“遗产美”,所以美学价值它都会包含。从遗产学的角度、立场出发,“民间文化”和“非遗”是分开来的,“民间文化”并不等于“非遗”。非遗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有鲜明的地域代表性。地域代表性非常重要。为什么各个地方文旅都要搞非遗?因为它有地域代表性。如果这个东西也能代表北京,天津就不会搞。所以首先非遗有鲜明的地域代表性;第二个非遗在历史上是一个有影响的东西,要传承有序。我们定非遗的时候,起码得有三代以上的传承谱系;第三个有较高的价值,我刚才讲了那五种价值,比如说美的价值、艺术的价值、历史的价值、文化的价值等;第四个是“活态”的。如果它不是活态的就不是非遗了,它只能进物质性的博物馆。如果现在还能造兵马俑,那肯定是非遗,如果你不能造,兵马俑就不是非遗了,而是物质文化遗产。现在依然是活态的,在传承中的,才是非遗,所以我们保护也是保护传承,也是保护活态,这是非遗保护的中心任务,核心任务。如果非要说“非遗美学”,我认为“非遗美学”本质上是指“民间审美”,因为非遗本质上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是民间的事物、民间的创造、民间的艺术,所以非遗审美的本质还是民间审美。非遗是民间文化里有代表性的东西,是最典型、最杰出、最高水平的文化,是历史上前辈创造的必须传承的文化。但是“审美”是它们共同的属性,所以非遗的审美本质上也是民间文化的审美,二者是没有区别的。如果有区别,就是非遗的审美比民间的审美更有代表性,达到更高的水准,所以我们说非遗审美跟民间审美是统一的,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强调的。◎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民间的美”和“民间怎么判断美”,就是“民间审美”刘 :先生说“非遗美学”就是一种“ 民间审美”,那什么是“ 民间审美”呢?冯:首先“审美”是两个字, “审”和“美”。“美”是客观的美本身。“审”是体验和判断,我们通过体验认为它美,或者是我们都认为它很美,这是你的判断。这两个搁在一起就是“审美”。我们说的“民间审美”的“美”是“民间美”,民间审美首先要包含“民间美”。美在民间是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地位的,我们生活一切都美,所以我们按照“民间美”的标准做出来一个“花样生活厅”, 展示一切民间生活都有美的创造。我们要把“民间美”解释清楚。“民间审美”有两层含义:一个审美是普通民间老百姓对美的判断,我喜欢我不喜欢,老百姓作出的一种取舍选择;另外一个审美是我们对民间文化的审美判断, 是我们要论述老百姓审美的特点,实际是我们的判断, 不是老百姓的审美;这是两种不同的“审美”。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民间的美”和“民间怎么判断美”,就是“民间审美”。◎ 民间审美是“自发”的、集体创造的、不断积累的“程式化”审美刘:对于民间审美的概念,先生已经阐释得非常清楚了。 您认为与精英美学相比,“民间审美”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呢?冯:美分两种,一种是“自觉的美”,一种是“自发的美”。民间的文化基本是“自发”的。不能说民间的文化没有自觉的,比如民间戏剧里怎么把人物演好了。他可能有自觉的东西,但是一般来讲民间是“自发的表达”。比如做一个布老虎,觉得搁这个颜色好看、鲜明,能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它是一个自发的东西,没有理性的艺术追求,没有理论。是单纯的直觉,是直接的夸张,是外向的张扬。而精英艺术跟民间文化不一样,他是用比较含蓄的方式来表达生命的本质。民间文化善于使用“谐音”的趣味化表达,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文化,并没有深意。所以民间画一条鱼就是“连年有余”,画个蝙蝠就是“幸福”,画一个鸡就是“吉祥”,画一个瓶子就是“平安”。因此,精英的审美是自觉的审美,是有理性追求的;民间的审美是自发的审美,没有理性思维过程,他觉得那么样美就这么做了。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强调一点,民间的美是“纯感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民间的美是集体创造的,它不是某个人创造的。比如杨柳青年画是杨柳青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共同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杨柳青年画才能够传下来。如果某个艺人在年画里边用了一块蓝,画在一个鱼的身上了,老百姓不认可这个蓝色,它早晚就没有,最后呈现出来的所有的审美成分都是老百姓认可的,所以它是集体创造的。底下跟着就来了第三个特点:民间的审美是不断积累的,是一代一代人积累下来的,它不是个人的艺术。比如齐白石死了,他的东西可以传给他的学生或他的崇拜者,或者是追随者,但是齐白石本人的艺术完结了。但民间艺术始终流传,为什么流传?因为它是积累的。还有第四个民间审美的特点就出来了:民间审美是“程式化”的,民间的审美没有理论,但是它有“程式”、有“口诀”。比如说“红配绿一块肉”,“黄配紫必定死”,黄和紫在一块不行,因为两个颜色就不能放在一起,他有这样的“口诀”,这个口诀就是一种“程式”,它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这也是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区别。◎ 非遗不仅是我生命的东西,它是一个民族生命的东西刘:先生在二十多年的非遗保护过程中撰写了大量非遗审美的文章,通过反复研读您的文章,我把您的非遗美学思想归纳为:民间情感之美论、 生命之美论、历史之美论、地域之美论,不知道先生是否认可?冯:你说民间的美学思想是民间情感之美、生命之美、历史之美、地域之美,我认为你总结得非常好。这些东西我认为才是最根本的东西,非遗美学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不是一个纯理论的东西。我做文化遗产抢救,不是从学者的立场做的,我是从作家的角度,因为作家把它看得跟自己的生命一样,所以说非遗跟我的关系是生命性的关系,它不是一般的我必须做、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只是“应该做”,那么我可以不做,因为我也可以找到一个别的也应该做的东西就可以把它代替了。因为它是生命性的东西,我觉得不能失去。非遗不仅是我生命的东西,它是一个民族生命的东西,甚至是人类生命的东西,每个民族都要保护。而且我认为做这个事儿比我自己写作重要得多,尽管我写作也是从内心出发的。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来自我自己的,动了我的感情了,我开始做这个事儿;二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我通过思考认为从更高的理性上看它意义更重大,我会把它做得更多、更具体、更深入,这是一个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刘:先生对民间文化的情感确实是发自肺腑的。说到“情感”,精英艺术也讲究情感表达,比如先生画“现代文人画”表达您作为现代文人的情感、 美学中也有“ 以情为本” 的理论,您认为民间文化中所蕴含的“情感之美”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冯:民间的审美跟精英的审美是不一样的,民间审美是直接的,因为民间文化是生活文化,先有生活的情感,然后这生活的情感需要表达,这个表达不是艺术自觉的表达,而是一种文化最本质的、最本能的、自发的表达,而且带有原始性的一种表达。所以为什么现当代的艺术家,不从人类文化史的各个历史时期里边拿东西,他们不学文艺复兴,也不学米开朗基罗,也不学巴洛克,也不学洛可可,也不学印象派,谁都不学,历史上凡是已经成型的文化形态一律都不学,直接找本源就找两个东西:一个找原始,一个找民间。因为民间和原始是共通的,不是共同的,是共通的。什么共通?它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它是非理性的,是本能的。现代人受文化教育或者是文化影响之后,有很多东西已经不是自己本能的了。民间文化是天真无邪地把情感直接表达出来的,所以民间的艺术是从生活里直接、自发地表达出来,他们表达的不是生活的思想,而是生活的情感。着火了,他们就把火神画出来,他们心里想让那火神是什么样的就画什么样,所以民间各地方画的火神都不一样,他就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画。所以我说它是最本质、最本能的。他们自发地表达生活的情感,所以他用的颜色也好,造型也好,线条也好,语言也好,都是他自己的审美,这种审美的本质是原始的。所以我为什么把我们博物馆那个厅就叫“花样生活厅”,它(民间生活)像花一样的生活,所有的表达都是一种审美的表达。民间的东西首先就是审美表达。审美是人的一种本质,人这种高级动物,他有这种本质,但是这种本质是最原始、最单纯的,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审美是人的本性之一。◎ 时间把历史内容注入物体中,使之呈现出特有的历史精神和文化,过后就变为一种“历史美”刘:如先生所说, 民间文化的情感是最原始、最单纯也最能打动人的。所以我们要传承它。此外,先生非常看重非遗的“历史美”, 您认为什么是“历史感”“历史美”?冯:非遗非常重要的是它的“历史美”。非遗美学有一定历史的含义在里面,有时间的含义,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美,它是时间创造的,时间在不同的材质上留下不同印痕。我们过去叫两种美:一种叫“传世的美”,一个铜器或者一个瓷器在手里抚摸过,表面有一层光亮,会有“包浆”,雕刻的线条会变得含混,会有一种含混的、模糊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一个岁月感,一个“传世的美”;另外一个是“出土的美”,比如一个器物在地下受到水的浸润腐蚀之后,它也剥落了,这个东西的美我们管它叫“出土的美”。这两种美都是时间造成的。如果它是一个物质性的事物,因为它材质不同,它有不同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岁月造成的, 形成一种特有的岁月的魔力, 岁月的印痕,这种美就是“历史美”。比如说一个古建筑,文艺复兴时期跟巴洛克时期留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不仅是形式不一样,年头不一样,文艺复兴的建筑一定更有沧桑感,更有岁月感,我用了一个词是:“历史感”。我写过一篇文章《城市的历史美》,说“历史感”就是“历史美”,历史感不是物品原有的,是历史的一种加工,时间把历史内容注入物体中,使之呈现出特有的历史精神和文化,过后就变为一种“历史美”。比如物品上的斑驳和残破即为“历史美”的所在。非遗中蕴含的历史传承、文化积淀也是“历史美”。因为它是遗产,经过漫长的时间磨砺,有岁月的沧桑感,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跟新鲜事物不一样的美,遗产的美实际就是一种“历史美”。时间的意义是“历史美”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形成“历史美”的先决条件。非遗的“历史美”还有特定时代的精神与文化,是某一个时代人们共同的审美。每个时代有特定时代的独特的美感,无论是有形的,还有无形的美,那个时代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审美。这个审美既有地域性的一面,也有历史时期的一面,地域是方位的、地理的;历史是时间性的,有不同的地域里边不同时期的一种美。比如民国时期的音乐有一种独特的美,当时你不见得能够听得出来,等过后它改变了,你才知道那个声音、那种旋律、那种唱法是那个时代的。从审美来讲时间性也是一种美,就跟一个人的相貌一样,刚生下来的样子不是他永远的样子,到了40岁、50岁都不一样了,经过一些磨难,人脸还要发生变化,它是时间改变的,时间改变的时候它的美是要变化的,但是它原有的本质的东西不会变。在历史中经过不断地嬗变,慢慢成熟起来被大家公认了的非遗的艺术审美价值非常高。◎ 非遗最重要的是“地域的代表性”,这个是它的精髓刘:非遗除了时间形成的历史积淀的美,还有空间形成的不同地域的美。先生为什么特别关注民间审美的“地域性”?
冯:非遗最重要的是“地域的代表性”,这个是它的精髓。比如说苏州桃花坞年画,有苏州地域的代表性。当然任何民间文化、民间艺术都有代表性,但是非遗特别强调的首先是地域的代表性,就是“地域性”。而且它有“典型性”,甚至于有“标志性”,我们才能确定它是必须传承的遗产。它的价值体现在这些方面,所以它更具有一种地域的审美特征。研究民间的审美,就必须研究它地域的审美特征。最近我给中央写了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几条意见,其中一条就是说一个村落的地域的代表性、地域的特征。我们对于传统村落认定,从来没有对传统村落的地域性进行确认,随着现在文旅结合开发,很多地方的地域性已经没有了,都是从别的地方搬去的, 村落自身的价值不知不觉消失了,最后变成“千村一面”,失去了古村落的保护价值,而且也没有旅游价值。刘:是呀, 因为对非遗的审美价值认识不足会导致对非遗的保护出现偏差, 因此先生提出要对非遗进行“科学保护”。在非遗美育方面,先生提出“ 学院博物馆化”的教育理念, 您是如何通过博物馆教育来提高学生审美的呢?冯:我们的生活中、文化里有大量非遗的美的东西,有审美价值的东西,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它,我们做非遗学需要知道非遗的审美价值。学院的这两个博物馆就是我在民间浩如烟海的生活里挑选出有文化价值的东西,把它集中起来,按照一个逻辑把它展示出来。非遗教育必须让学生认识非遗的价值。一个文化遗产,它的文化价值,它的地域价值,我们都可以告诉他,可以分析,可以通过看书研究讨论,老师也可以把这些道理讲给他,跟他一起讨论。但是审美价值不同,审美价值光讲道理是不行的,因为美是需要体验的,需要感受的,有了体验和感受,然后一点一点地产生对非遗的认识,需要有一个升华的过程。通过感受变成一种认知,变成一种理性的东西,这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很重要,就要对他进行熏陶。非遗的整个审美教育的过程离不开对他一点一滴地熏陶,不定哪一天他忽然有了悟性了,他感受到了明白了非遗的美。在这种环境下,学生们需要一种熏陶。所以我的一个教育理念就是“把学院博物馆化”。常和艺术品在一起的人,他们就会有修养,因为人的美不仅是视觉的美,艺术品会影响他们行为的美、气质的美,所以这对我非常重要。我到学院就把我的收藏都搬进来,建好一个小博物馆,把艺术品从外边到里边放了好些东西,越放越多,放来放去,我觉得咱们学院的人就跟外边人也不一样,跟别的学院的人不一样。另外我觉得它会影响学生,会影响他们到别的地方也会注意艺术,注意不同的文化,注意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东西的内涵。这是一个慢慢熏陶的过程。这些孩子们到了学院来,就要到博物馆去。审美的东西不是教出来的,艺术跟你的趣味是一致的,这是心灵上的东西,是心灵要求,最重要的是熏陶。我们给他们创造这样的土壤环境,让他们跟艺术品有很多接触,这是我的一个方式,也是我的一个想法。◎ 如果要保护传承非遗,就要保护和传承非遗美的价值刘:谢谢先生用心良苦给我们营造这么美的求学环境,在“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里可以充分感受到先生的美学思想:比如“ 民间雕塑厅”按照时间的顺序布置,体现出先生“历史美”的审美观 ;“花样生活厅”则表现出民间生活情感的美;“年画厅”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每个厅都能体现先生非遗美学的一个不同的审美观点。除此之外,先生对博物馆的每个细节安排也非常考究,记得2011年我有幸参加了木版年画十年展的布置筹备,亲眼看见先生调试灯光、布置展品,经过先生的调整,整个展厅的形式感、 情境、效果就都不一样了。冯:这就跟我画画一样,稍微颜色有一点不舒服就觉得难受极了。如果我们没有审美的需求,你说你热爱非遗,我就觉得有点怀疑。如果你不知道它哪个地方是真正美的,哪个地方是有价值的,或者是不可缺少的,那么你就不会保护它,可能过些日子这东西就没了,所以如果要保护它传承它,就要保护和传承这个美的价值。◎ 我们要挖掘非遗的美学价值和文化魅力,促使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热爱非遗刘:先生说得是,非遗的美学价值是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内容。我们只有认识到非遗的美才能发自内心地去热爱它,这也是我们研究非遗美学价值的原因。非遗美学目前是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您认为“非遗美学”的研究对非遗保护和非遗学科建设有什么意义?冯:非遗学是一个新建立的学科,很多问题都是新问题。你提出这个问题挺好,对学科的建设进行思考。非遗学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涉及很多方面的学科知识,比如美学就是一个大问题。非遗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它的美学价值,也就是它的审美价值。从非遗保护的立场来讲,人民对文化遗产的热爱是非遗保护的根本保障,而要想让人民热爱非遗,还要靠非遗本身的魅力来吸引人。非遗之所以会形成传统,被一代代人认同,一定是有好东西的,一定是美的,所以我们要挖掘非遗的美学价值,挖掘非遗的文化魅力,只有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热爱非遗,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遗。我们的非遗保护面临两个很大的问题。从客观来讲,人们历史上不重视它。时代的变化太快了,历史是不断除旧更新的一个过程,特别是民间的东西,人们不重视它。按民间文化的规律,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自生自灭,也就慢慢消亡了,所以需要挽救。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主观上我们没有文化的自觉。在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我说人类整个的文化历程有两个重大的改变,一个改变是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这时候艺术产生了,美也产生了,这是人类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由文化的自觉或者艺术的自觉变成自觉的文化保护。我们要有一个自觉的文化保护意识,但是我们没有,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很大。就审美来讲,我们的教育环境、我们的审美环境中 , 审美的教育这一套体系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人在审美上是有缺失的,而且缺失的是很重要的这一部分,它实际上是人的精神的一种缺失。所以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让大众能理解,希望我们做文化遗产保护的人,自己得有这种自觉,这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刘:非遗美学的研究确实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感谢先生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冯骥才,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作家、画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
刘明明,山东潍坊人,博士,海南大学风景园林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美术学。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间文艺论坛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