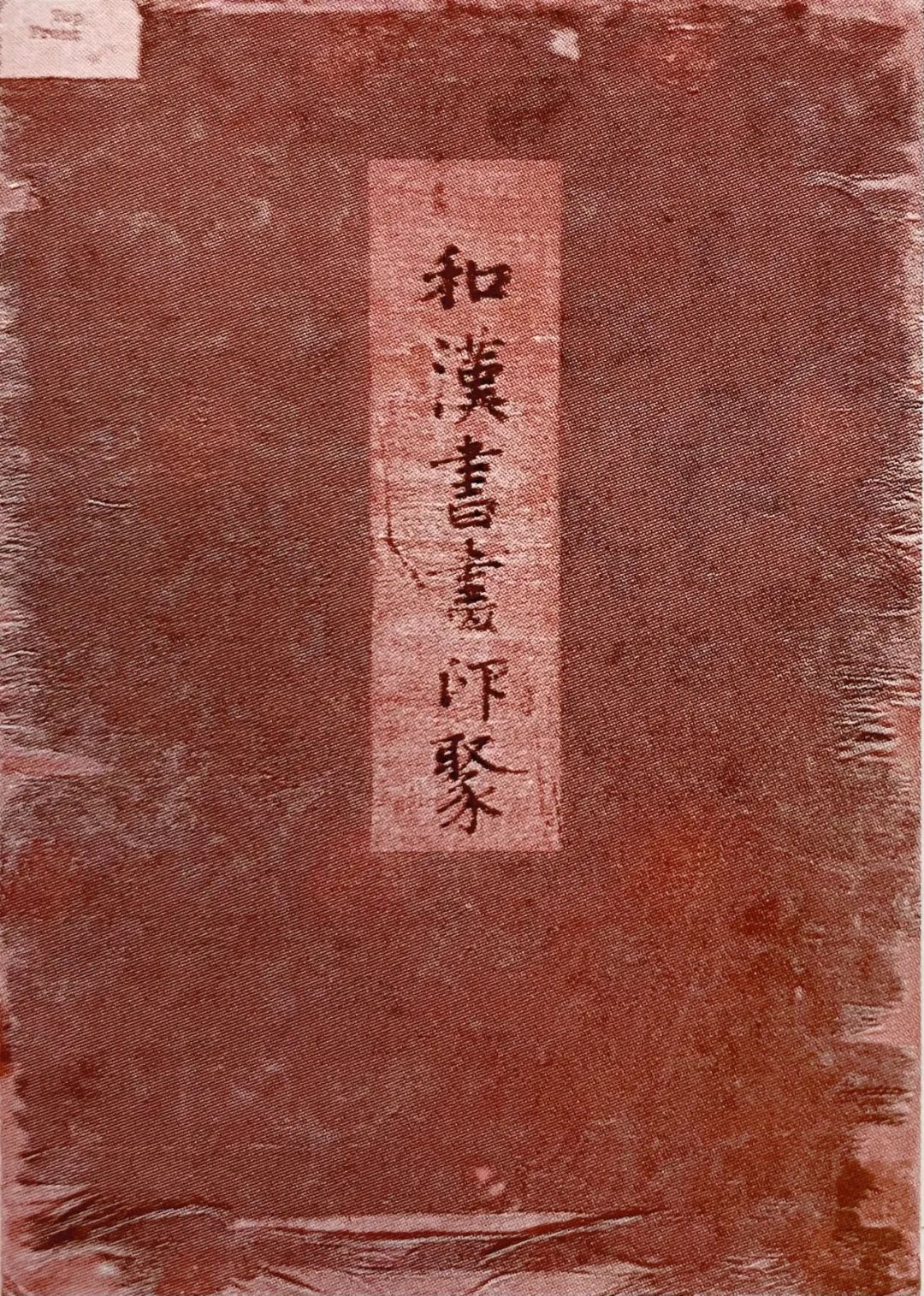一、中国的启示:西方19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多元视角西方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阶段。从早期探险家的游记手札,到几个世纪后耶稣会传寄回国的书简,中国被塑造成一个优于欧洲文明的“文化乌托邦”。自1811年法国学者雷慕沙(Abel Rémusat)出版了《中国语言文学论》(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rature chinoises),西人对中国的探索进入了学术领域。专业汉学时代开启后,汉学家们相对客观地研究了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但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导致了“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滋生,中国的形象被转换为“文化他者”,复杂的意识形态被隐蔽在其新学科体系的建制中。发展至19世纪末,中国艺术的研究也被纳入了汉学范畴。法国历史学家帕莱奥罗格(M. Paléologue)1887年出版《中国艺术》(L¡¯Art Chinois);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1896年出版《论中国艺术的外来影响》(Uber fremde Einflusse in der Chinesischen Kunst);英国汉学家波西尔(S. W. Bushell)1904年出版《中国美术》(Chinese Art);英国外交翻译家翟理思(Herbert A. Guiles)1905年出版《中国视觉艺术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这些早期学术成果作为汉学的补充,展现出依赖于文本翻译的特征,往往忽略了对艺术作品本身的释读。汉学家们用科普性的简述和有限的几幅插图,将关于中国艺术的知识输入西方。这种狭隘的研究取向,潜在助力了西方话语霸权,使阅读者难以领悟到中国艺术独特的美学价值。然而并非所有的中国研究都基于“东方主义”(orientalism)视角,同时代仍有部分学者以开放、平等的学术视野,真正意识到中国美术之于世界的价值与贡献,美国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即是如此,他对中国文化和美术的关注,根植于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的启示。费诺罗萨大胆质疑了隐藏在欧洲理性中的文化成见,试图从中国哲学思想中汲取灵感“为西体所用”,实现东西艺术的融合。1853年费诺罗萨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的塞勒姆,13岁时以预考第一的成绩进入哈佛大学专修哲学,其间他醉心于爱默生和斯宾塞的思想。毕业后又获得派克奖学金升学至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哲学。1878年费诺罗萨在机缘巧合下前往日本,在日旅居的12年间,他不断研读文献,鉴藏中国古画,开启了中国美术研究。1890年费氏入职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任日本部主任,多次在欧美国家策划以东亚美术为主题的讲座和展览。自1900年开始,其研究领域从中国美术拓展至汉诗,出版专著有《中日艺术的源流》(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等。在此过程中,费诺罗萨始终将中国视作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分子,甚至可担当指摘西方现代文明的“武器”,而非“他者”的落后形象。费氏曾说道:“在20世纪初,真正理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严肃的问题。经过往日的努力,我们获得了一些启发,然而却仍处于这一进程中相对早期的阶段。之后可能以我们从中国文明中获得更多的启示而告终,至少与我们给予它的是同样多的。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过去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未来影响的预示。对中国文化的探索不再停留于感兴趣的层面,而是变成了现实。”这段文字源自费诺罗萨写于1900年12月18日的文章《中国对西方的影响》(A History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a upon the Western World)。他回溯了汉、唐、元、清几个阶段中国文化的西方影响,厘清了中国文化于19世纪之前的西渐历程。文中举隅了门多萨(Mendoza,1545—1618)、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阿米奥(Amiot,1718—1793)、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钱伯斯(Chambers,1723—1796)等学者的著作,分析了中国文化元素是如何具体地进入欧洲文学艺术的构建之中,揭示出历史发生的丰富性。费诺罗萨用到“影响”一词,以古鉴今地预言了中国美术和文化介入20世纪西方世界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正如费氏对钱伯斯的赞许,“作为一名专门研究中日艺术的学生,我当然认同钱伯斯提出中国艺术优于西方的言论,那是真理的预言,只是早于时代150年。即使在今天,文学界也甚少有人能够意识到广阔的艺术视野,才具有最高价值。但他们将来一定会有所意会”。鉴于此,引介中国美术、传播中华审美价值以拓宽西方人的艺术视野,成为费诺罗萨远大学术理想中不可忽视的一环。1876年,美国费城举办了万国博览会,清政府受邀参展,在本馆设有一处展区。展陈的大量陶瓷器、漆器等工艺品及家具,成为费诺罗萨对中国美术的最初印象。1878年,在友人莫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1838—1925)的引荐下,费氏远赴日本,担任起了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的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教席。根据其妻子晚年的回忆录,“从第一年起,他就深深地迷上了令他耳目一新的美术——古老的日本美术。但还必须加上古老的中国美术,如果不对中国美术进行研究,对日本美术的研究就无从谈起”。于是,得益于助理有贺长雄(1860—1921)与冈仓天心(1863—1931)的文献收集和翻译,费诺罗萨逐渐对中国古代美术的发展史有了知识储备,能够清楚每个时期的代表画家及其笔墨特征。但他也绝非止步于文献阅读,从1878年至1882年间的演讲手稿,可以窥见费氏融贯西方哲学的学术理念,这种哲学根基有助于他对美术史和传统美学思想加以深入思辨。首先,费诺罗萨对于整个中国美术发展脉络有着异于传统认知的新思考。他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试图以“兴衰观”重构中国美术史。或因受到近代日本鉴藏观的浸染,也因局限于19世纪末日本不完善的中国绘画收藏体系,费氏将中国美术的发展巅峰界定在唐朝和宋朝。他写道:“在中国初唐时期,天下大同,佛教、道教、儒教的创造性势力达到了高潮。因此人们注意到了吴道子等画家。”至于宋朝,则“出现了各种艺术风格和优秀的一流画家们”,并反复提及南宋画家夏圭,称赞其山水画构图之精妙,可为古代绘画的典范,亦是阐释美术本质的最佳范例。他还将李龙眠、牧溪与吴道子并论,视之为后世佛教画家不可逾越的丰碑。他在1882年的著名演讲《美术真说》以及晚年著作《中日艺术的源流》中,均重述了这样的中国美术史观。这影响了西方一众美术史论家,并引发了20世纪上半叶海外宋元画的收藏热潮。在另一篇名为《关于美术的连续演讲之主旨》的演讲笔稿中,费诺罗萨写下了对中国绘画理论的思考。他将“气韵”这一范畴翻译为“Spirit”,相异于后来20世纪英语学界的主流译法——“rhythm”(节奏)。对此他解释道:“宋代郭若虚的观点与我一致,‘气韵’这种特征指的是精神之优越性,也就是我所说的‘妙想性’(ideality)。一切笔墨和技法都源于气韵,要以之为核心,笔墨和技法相互交融,才能成就一幅佳作。”他晚年在专著中进一步解说:“‘气韵’是第一个汉语(美学)范畴,指绘画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描绘的对象栩栩欲生,充满了生命力。”费诺罗萨依据黑格尔的美学思想,把艺术的本质定义为“妙想”(idea)。他也将“气韵”等同于“妙想”,并偏重于其中的精神内涵,这代表着他充分意识到了中国美术的审美价值。不过费诺罗萨对“六法”理论也非全然认可,又称:“它并不是基于科学的原则演绎而来,既不均衡也不完善,只是中国评论家们依据经验的拼凑。为了使之成为绘画的科学性原则,须科学地阐释六法。”因此,在西方美学话语体系下,费诺罗萨将西人难以理解的“六法”演变为“十格”,凝练出“线条”“浓淡”“色彩”“旨趣”四大品鉴范畴,日后在美国各地的讲座中,他也曾多次系统性地宣讲论述之。费氏开创了一种新的视觉审美模式,努力探问中西美术相似的底层逻辑,“使西方人能够像接受欧洲艺术流派那样,毫不费力地欣赏颇具神秘色彩的亚洲艺术”。足以见得,他对“六法”的现代阐释,为当时西方人欣赏中国绘画提供了理论指引。其次,费氏对中国美术的文化特征也有所领悟。他谈及过诗画相融,“在中国,诗和绘画的主题往往是相似的。实际上可以将绘画的本质,看作是诗歌以绘画的形式再现”。中国绘画,尤其是山水画,不同于西方写实艺术,精髓在于意韵的传递。费诺罗萨对诗歌的关注,无疑加深了他对中国绘画意境的感知,也是其晚年研究汉诗的肇始。同时他明白了中华美术“书画同源”的传统属性,“西方绘画起源于雕塑,东方绘画则源自书法,这虽是笼统的理论,却极具真实性,它从根本上诠释了东西方艺术各自的特殊性。东方绘画的优越之处在于书法式的运笔,而这一点也最难为欧洲人所理解”。接着他又说道,“不能将绘画等同于书法。绘画是从书法中派生出来的,但‘笔法’并非其唯一要素,还发展出了色彩、浓淡等其他特质,也是值得被探究的”。这一时期,费诺罗萨还亲自拓印和收藏了上百个中国画家的印章(图1),并将之与日本画家的印章放在一起,亲自手工制作了一本《和汉书画印聚》(图2),只可惜他对钤印未作过任何理论研究。

图1 费诺罗萨收藏的中国画家印章 出自费诺罗萨著,村形明子编辑和翻译:《欧内斯特·费诺罗萨文集》(第二卷),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1987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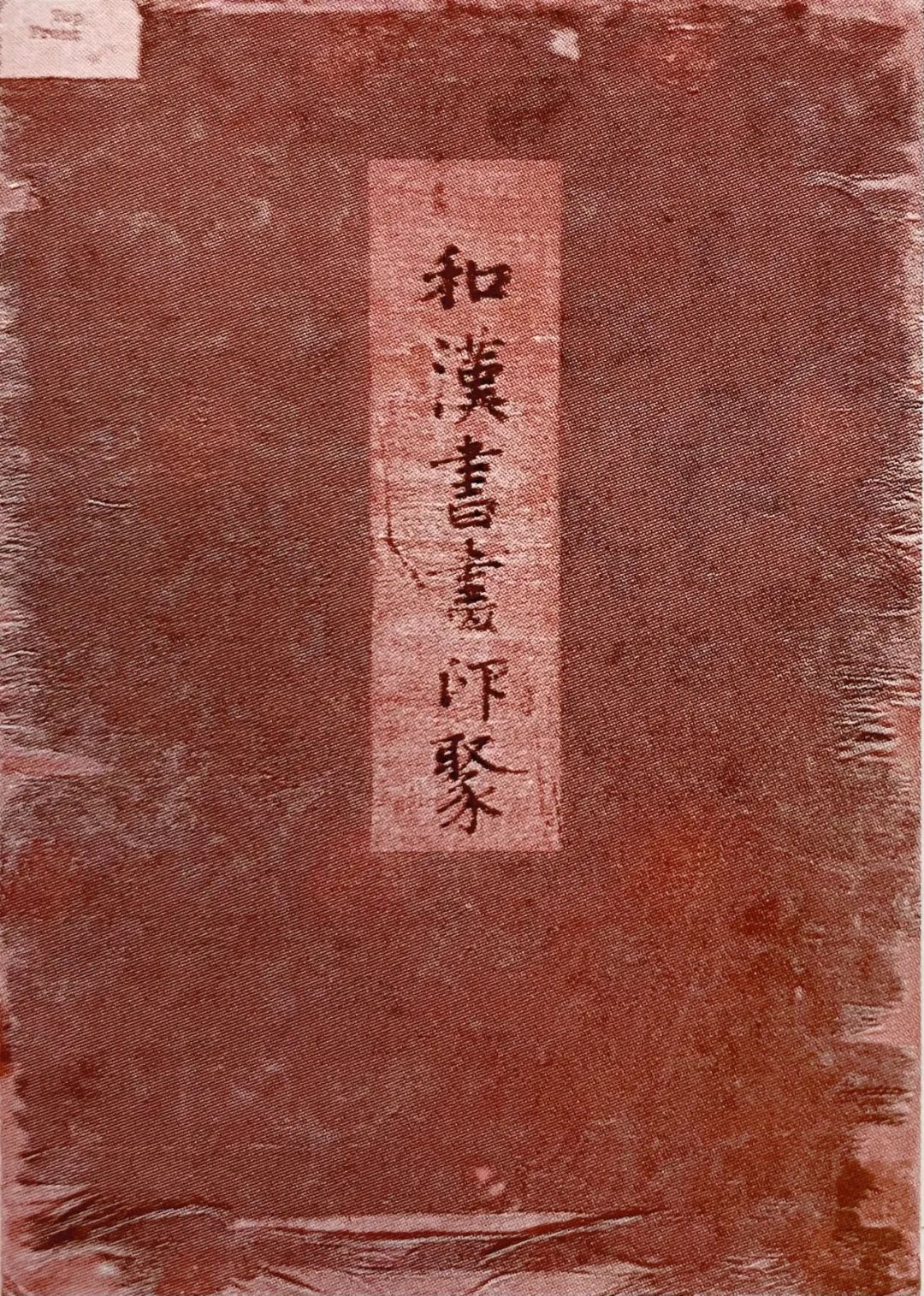
图2 《和汉书画印聚》封面 出自费诺罗萨著,村形明子编辑和翻译:《欧内斯特·费诺罗萨文集》(第二卷),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1987年版
若将目光聚焦于费诺罗萨早期文稿中的中国美术部分,可以发现他在日本文化的熏陶下并未一叶障目,而是很早就以批判性的态度处理史料,同时开启了对中国美术的初步研究。除了早先的观展经验外,作为西方学者的费氏已经认识到中国审美价值的独特性并开启了其学术溯源之旅。自1880年始,费诺罗萨在冈仓天心的陪伴下,利用教学闲暇时间,多次前往关西的古社寺进行宝物调查,并在1884年加入了日本文部省创设的“图画教育调查会”,受命进一步清点古寺所藏的历代珍宝。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保存了两份费氏的考察笔记,其中对中国画的记录占据了主要篇幅。根据统计,他集中考察了京都和奈良的11处区域,所观览的中国古画多达300幅,以日本“古渡”时期的收藏为主,包括吴道子、宋徽宗、李龙眠、马远、牧溪、颜辉、吕纪、仇英、林良等大家之作,这无疑为巩固他的中国美术史观提供了足够的视觉经验。在考察过程中,费诺罗萨驻足于每一幅画作,品味其中的构图、色彩与笔墨细节,并对之做出好恶评断。他甚至大胆运用美术史知识,以类似风格学的方法重新断代了不少古画。不过,碍于所见实物有限,他对中国绘画的风格史建构存有偏差,断代结果往往被后世学者推翻。这一期间,令费诺罗萨大为震撼的画作,是大德寺所藏的牧溪《观音图》以及东福寺藏吴道子(传)的《释迦如来图》。次年5月3日,他以《采用佛教主题的得失》为题,在日本“鉴画会”上演讲,且将这两幅画奉为古代佛教美术之圭臬,盛赞吴道子和牧溪创造了后人无法跨越的巅峰。他形容牧溪笔下观音的衣纹样式,以及吴道子描绘释迦如来的“莼菜条”笔法,皆做到了精练纯粹、一气呵成。这是后来日本画家兆殿司、雪舟、相阿弥等人无法达到的境界,“他们笔下的佛像不过是抽象而优雅的曲线、笔致,线条之下无法感知到观音的灵魂。吴道子犹如巨人刷毛般的笔锋,既是男性肉身力量的真实表现,又呈现出艺术性上无与伦比的遒劲之美。这两幅佛像画淋漓尽致地展露出佛像的神性,正是视觉艺术与精神法则,早已在画家笔下合为一体了”。对于考察中遇见的其他唐宋绘画真迹,费氏虽没有过多的文字评述,但也均评级为优品。除单纯的形式分析外,他还临摹过数幅中国绘画,对其中3幅写下了长篇临摹心得。第一件是在8月6日考察高台寺时,临写的禅月大师(贯休)的《十六罗汉图》(图3至图5)。他评定其中有3幅优品和2幅良品,逐一描述了这5幅画面的内容,包括罗汉的姿势、袈裟的用色以及背景树石的画法。费诺罗萨临摹了那3幅优品,用简单却富有变化的线条,极速勾勒出罗汉的姿态,其隆鼻朵颐、胡貌梵像,颇具“禅月式”风格。第2幅则是同一天考察泉涌寺时,临摹的宋徽宗所作《释迦文殊普贤像》。其笔记中写道:“彩色部分剥落较多,但整体形式仍十分精美。部分纹样风格显然是中国式而非日本式的。虽然称不上是杰作,亦实属优品。其中文殊的画像最为完善,背景岩石的皴法也做到了无可挑剔。该画家风格继承了吴道子、李龙眠和张思恭,但也呈现出独特个性。”第3幅则是在8月7日考察本法寺时,所见到的钱选《莲花图》,费诺罗萨不禁赞叹是“伟大的经典之作”“硕大的红莲、荷叶画得十分真挚,略显生硬却又古拙的样式与明代风格不尽相同,是我所见过的红莲图中最佳。将该画上溯至舜拳,确是名副其实”。
图3 左侧为原作 贯休《十六罗汉图》(宋摹本)绢本设色 129.1cm×65.7cm 宋代 日本高台寺藏;右侧为费诺罗萨的摹本 出自费诺罗萨著,村形明子编辑和翻译:《欧内斯特·费诺罗萨文集》(第一卷),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1987年版

图4 左侧为原作 贯休《十六罗汉图之一》(宋摹本)绢本设色 129.1cm×65.7cm 宋代 日本高台寺藏;右侧为费诺罗萨的摹本 出自费诺罗萨著,村形明子编辑和翻译:《欧内斯特·费诺罗萨文集》(第一卷),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1987年版

图5 左侧为原作 贯休《十六罗汉图》(宋摹本)绢本设色 129.1cm×65.7cm 宋代 日本高台寺藏;右侧为费诺罗萨的摹本 出自费诺罗萨著,村形明子编辑和翻译:《欧内斯特·费诺罗萨文集》(第一卷),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1987年版
短期内密集的艺术品鉴和临画实践,使费诺罗萨沉浸于大批中国美术作品实物之中,触发了崭新而强烈的审美体验,这是其艺术品位优于同时代汉学家的缘由。对中国绘画风格的探索与仿效,成为其审美经验的累积。而他对佛教绘画的偏爱与沉迷,使他在1884年改宗佛教成为居士,这一信仰上的皈依似乎已预示了他返回美国后所从事的美术活动的方向。在12年的旅日经历中,费诺罗萨借“日本之眼”,发觉中国美术的审美价值,明确认识到在世界文明未来的发展中,整个东方美术不仅会提供珍贵的图像资源,亦能起到精神指引上的巨大作用。面对一无所知的西方观众,中国美术的输入显得十分迫切和笃定,这一努力最终成就了费诺罗萨在美国的艺术事业。须要强调的是,因受制于认知局限和西方思维,费氏眼中的“中国美术”并非原本意义,换言之,他对中华审美价值的转译具有片面性。他的鼓吹好比一把双刃剑,既树立了新的审美标准,为中国绘画进入世界艺术地图开辟了道路,却也在无形中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有关中华美术经典的误读版本。商勇,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秦艺心,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