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 > 论坛研究
研究 | 胡斌:跨历史与跨文化视角的中国美术现代化研究断想(二)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3-10-28 浏览量:5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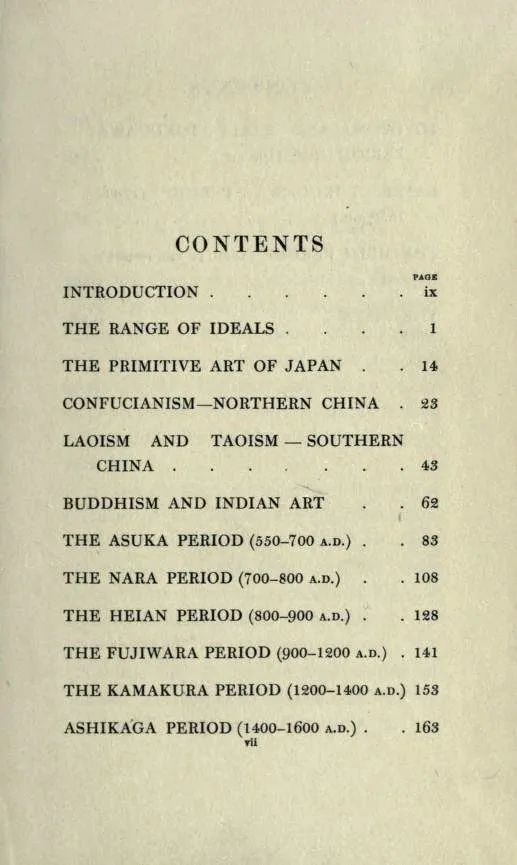
图6 [日]冈仓天心《东方的理想》目录,1903年

图7 刘松甫出品、[美]爱诗客编辑:
《中国古今名人图画录》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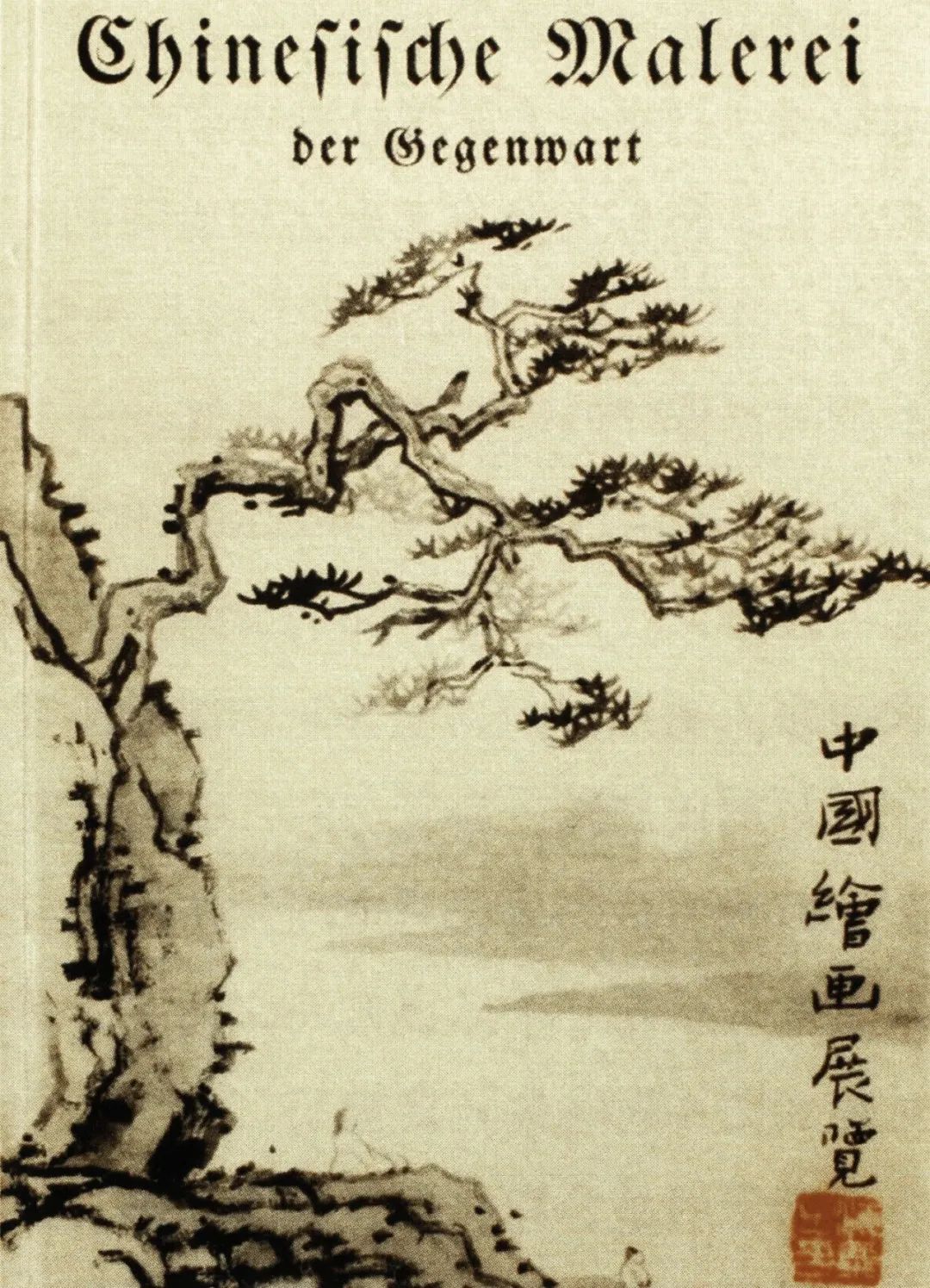
图8 《中国绘画》展览图录,193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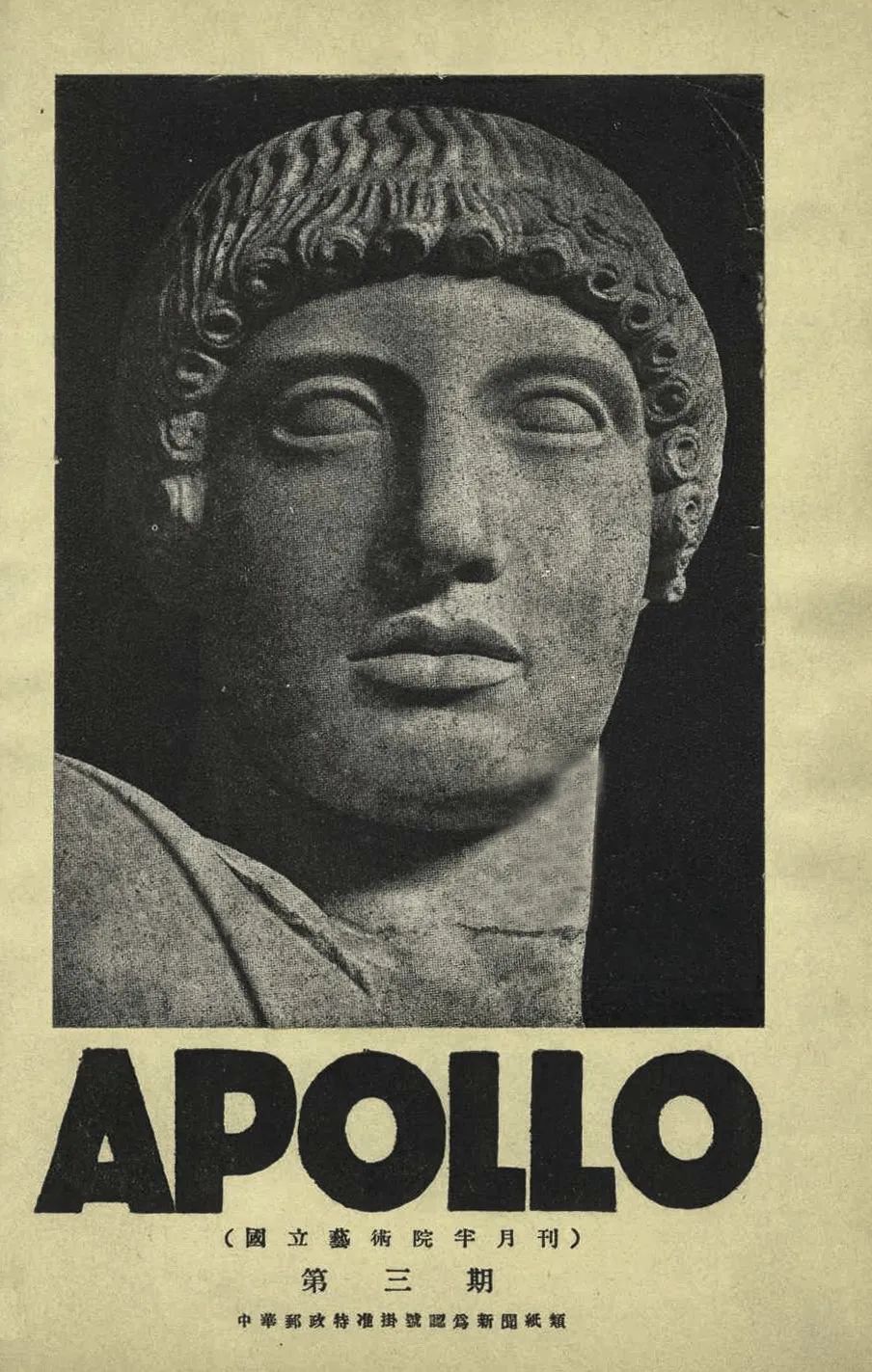
图9 国立艺术院月刊《亚波罗》1928年第3期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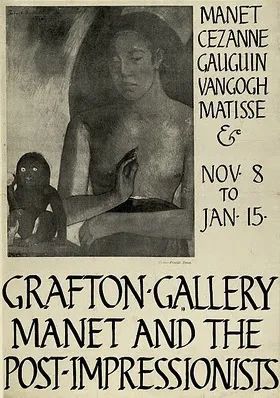
图10 “马奈与后印象派”展览海报,1910年

图11 林风眠《戏曲人物(佩剑仕女)》纸本水墨
32.8cm×33cm 20世纪50年代初期 香港艺术馆

图12 张仃《公鸡与小鸡》纸本水墨
46cm×35cm 20世纪60年代初期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美术杂志社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