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 > 论坛研究
研究 | 胡斌:跨历史与跨文化视角的中国美术现代化研究断想(一)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3-10-27 浏览量:402

图1 《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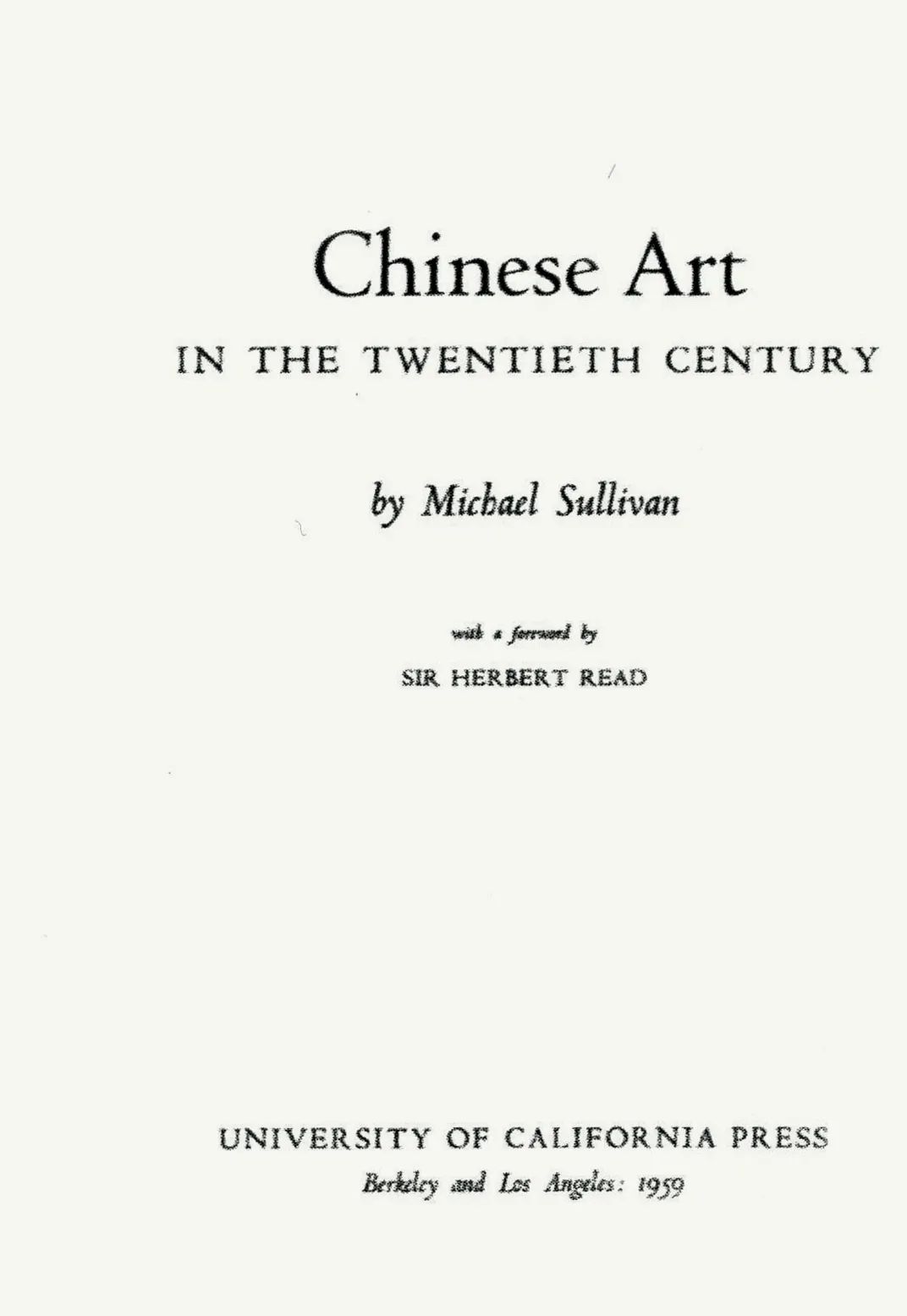
图2 [英]苏立文《20世纪中国艺术》,19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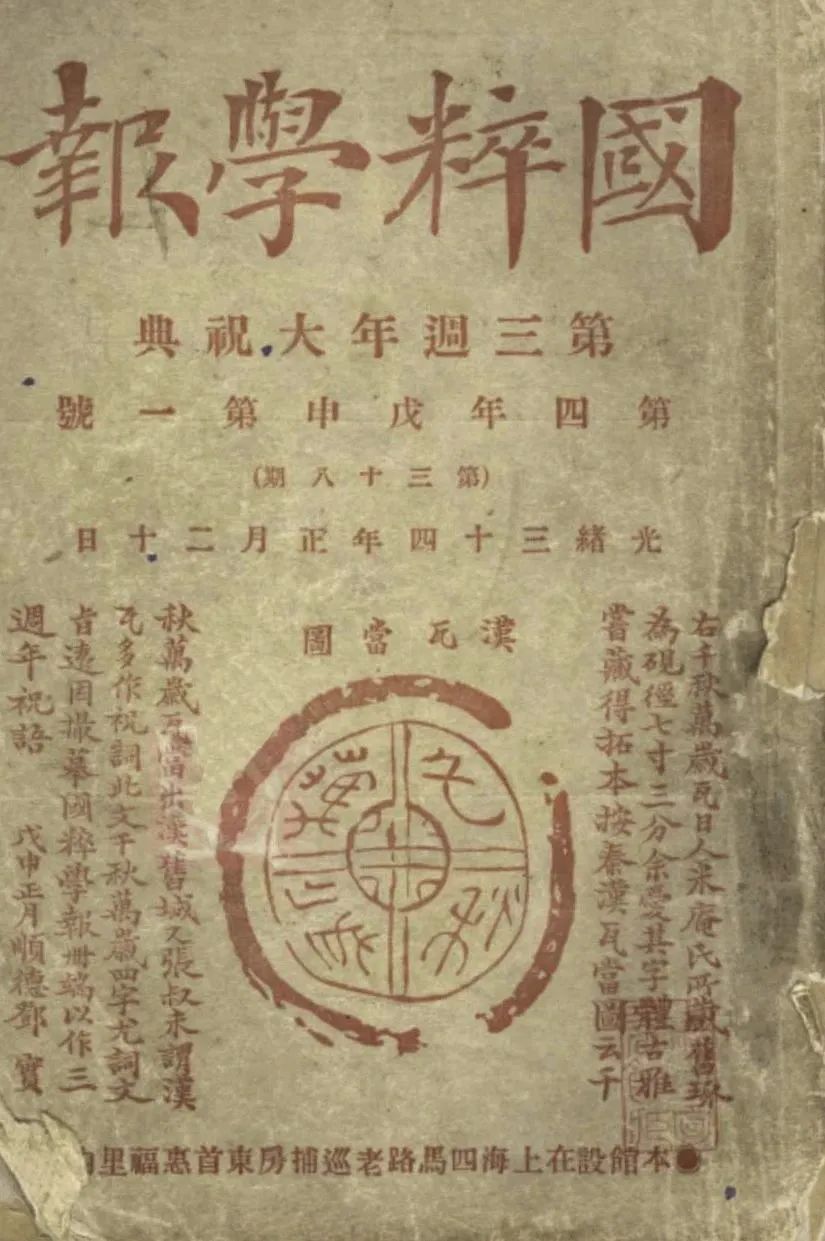
图3 《国粹学报》1908年第1期

图4 庞薰琹《盛装》纸本水彩 1942年 中国美术馆

图5 苏天赐《蓝衣女像》布面油画 73cm×51cm 1948年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美术杂志社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