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高建平丨从“三大体系”看美学与艺术学体系异同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时间:2025-07-15 浏览量:557
美学与艺术学在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上有同有异。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其体系是从哲学体系引申而来的,与哲学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学家们常常从一些基本的理论预设出发,推导出美学的理论体系,因而先有美学的学术体系,后有美学的学科体系。与美学的体系建构路径不同,艺术学则首先建立的是学科体系。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一般”,而“艺术一般”的形成,依赖于“美的艺术”组合的形成,也依赖于对这一组合中的“同一原理”的寻找。艺术学体系的形成,受到美学体系的深刻影响。艺术学的“三大体系”建设,是在学科体系建设和完善的基础上,形成学术体系并发展话语体系。
一、“美学”的提出及其体系建构
当然,严格来说,美学不是鲍姆加登一个人创立的。18世纪,许多理论家都曾对这个学科的形成作出过贡献,例如意大利人维柯提出“诗性思维”,英国人夏夫茨伯里提出“审美无功利”和“内在感官”说,博克对“崇高”与“美”的对立做了论述,休谟对“趣味”进行了深入分析,法国人夏尔·巴托提出了“美的艺术”的组合,直到康德从一个独特的哲学视角将这些概念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康德在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正在于此——从他开始,美学体系被完整地建构起来了。
欧洲美学史,都是从古希腊开始写起。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如此,伯纳德·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的《美学史》,K. E.吉尔伯特(K. E. Gilbert)和H. 库恩(H. Kuhn)的《美学史》,以及笔者翻译的门罗·C. 比厄斯利(Monroe C. Beardsley)的《美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代》,也都如此。然而,在古希腊时并没有美学体系,也没有Aesthetica这个名称。我们所看到的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分散在他所写的各种对话中,这些关于“美”和“艺术”的论述被后人集中起来编辑成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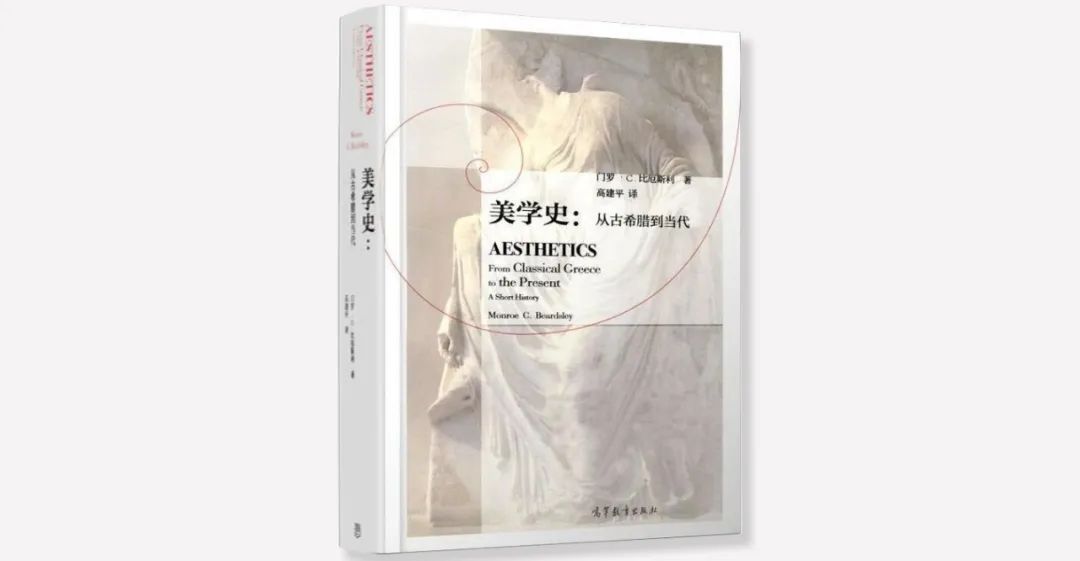 [美] 门罗·比厄斯利:《美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代》,高建平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版。
[美] 门罗·比厄斯利:《美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代》,高建平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版。
朱光潜一方面说美学起源于鲍姆加登,另一方面又说古希腊时期就有美学。对于这一稍显自相矛盾的说法,他在晚年写的一本名为《美学拾穗集》的书中,特意谈到要区分两个概念,即“美学思想”(aesthetic ideas)与“美学”(aesthetics)。他指出:
在西方,自从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在1750年发表他的《埃斯特踢克》(Aesthetik)即《美学》之日起,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虽不过两百多年,美学思想却与人类历史一样的古老。
“美学”这个学科自建立之初起,就是哲学体系的一部分。鲍姆加登从其所属的哲学体系来看,是一位理性主义哲学家,他深受沃尔夫的影响,而沃尔夫又受到莱布尼茨的影响。鲍姆加登正是在理性主义哲学之下,寻找感性的相对独立性,提出了美学是感性学,进而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
“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这一属性和特点被后来的哲学家们保留了下来。康德在建构他的哲学体系时,先写《纯粹理性批判》,后写《实践理性批判》,最后才写了论述审美和审目的判断的《判断力批判》。那么,究竟《判断力批判》是连接前两个“批判”的桥梁,还是康德的哲学大厦的穹顶?在康德的论述中,他更强调其“中介”作用。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论”中,康德指出:“各种认识能力的协调一致包含着愉快的根据,这些认识能力的游戏中的自发性使得上述概念适用于作自然概念的领域与自由概念在其后果中联结的中介,因为这种联结同时促进了心灵对道德情感的感受性。”他强调对审美与审美目的的判断在自然与自由之间的中介性,正是通过对这种中介性的阐释,康德完成了其哲学体系建构。
由此可见,美学体系从属于哲学体系,是从哲学体系中推导出来的。联系到我们现在谈的“三大体系”,即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其中学术体系建设,以系统性学术著作的出现为成熟标志;学科体系建设,以这门学科的各种知识被编订为优秀的教材为成熟标志;而话语体系建设,则以这门学科的范畴、概念、术语和关键词的整理、研究和完善为标志。关于“三大体系”的建构过程,在美学上,应该是以学术体系的建立为先导,从哲学体系推导出美学体系,在出现了成体系的美学论著之后,才有作为学科支撑的美学教材,以及服从于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话语体系。
美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是一门“老年人”的学问。康德66岁时才发表《判断力批判》。黑格尔61岁逝世,《美学讲演录》是在他去世后,他的学生根据其讲稿整理出版的。维特根斯坦甚至没有活到他的“美学时期”,也没有留下美学专著,然而,他的后继者却根据其思想发展出一个蔚为大观的分析美学学派。我们所熟悉的门罗·C. 比厄斯利、阿瑟·丹托、乔治·迪基和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等人,都属于分析美学学派。杜威的《艺术即经验》,是根据他1932年在哈佛大学的讲演,于1934年(杜威时年75岁)修订整理出版。许多重要的哲学家,都是在他们的哲学思想已经成熟之时,感觉有所欠缺,于是写出了美学著作。这种现象说明,一些经典的、重要的美学体系常常是从哲学体系推导来的。由此也可从侧面说明,为何在美学上学术体系在先、学科体系在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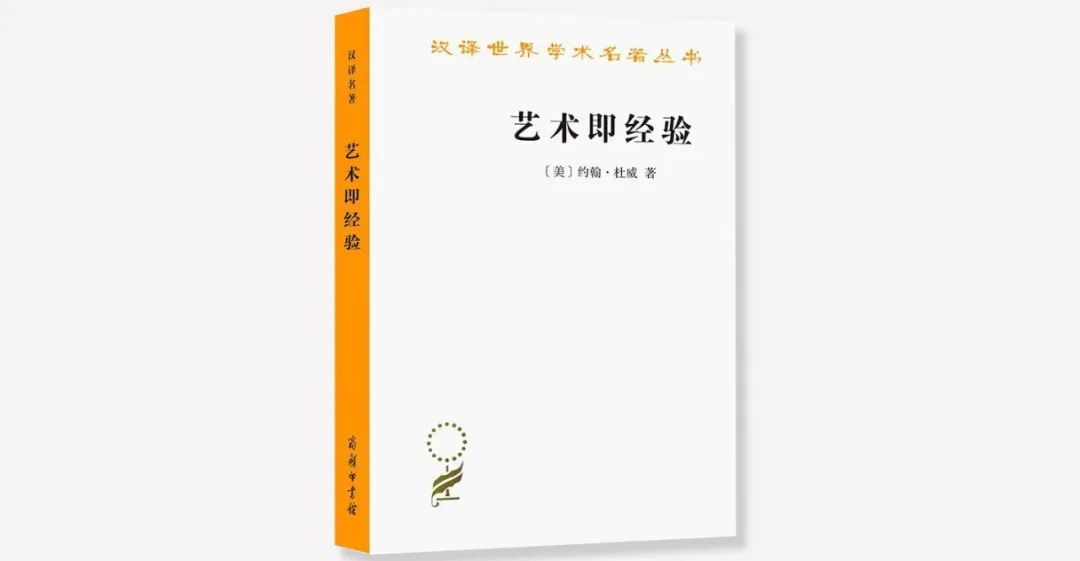 [美] 约翰·杜威 :《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
[美] 约翰·杜威 :《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美学体系的建构,一般来说,都是从美开始,进而涉及艺术的。鲍姆加登开始讲“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计划从这个定义出发,推而广之各门艺术。然而,他在1750年写出《美学》第一卷后,因为身体原因到1758年才出版第二卷,1759年便去世了,原本计划写五卷的《美学》最终没有完成。
康德在66岁(1790)时出版了《判断力批判》。这本书首先谈美及美的四个契机,并设立一种“纯粹美”,认为这种纯粹美是无功利的。后来,他发现美与功利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提出了“依存美”。当他解释“审美无功利”之时,又将美说成是“知解力”与“想象力”的和谐运动。“知解力”来自“纯粹理性”,而“想象力”则来自“实践理性”。又如康德在讨论“崇高”概念时,关涉到“自然”,这其实是继承了英国美学的传统。“崇高”这个概念,在17至18世纪的法国人那里,主要被用于评价艺术。法国文学理论家布瓦洛将朗吉弩斯的《论崇高》译为法文,用来形容类似高乃依和拉辛戏剧中道德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崇高”这个词被用来指涉自然,是从英国开始的。18世纪初,有三位著名的英国人分别去了阿尔卑斯山,他们分别是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夏夫茨伯里第三伯爵(3rd Earl of Salisbury)、约瑟夫·爱迪生(Joseph Addison),他们的游记都记录了由阿尔卑斯山所产生的崇高之感,这构成了崇高的现代含义。中国人用“崇高”二字来翻译the sublime,是非常恰当的。崇山峻岭总是能给人以崇高之感。后来,博克举了许多自然和生活中的例子来加以说明,诸如崇高是大的、美是小的,崇高是粗糙的、美是光滑的,等等。博克成了从夏夫茨伯里等人到康德的中介。到了康德那里,才有所谓数的崇高和力的崇高。虽然“崇高”的概念是从英国美学中接受而来,但康德很好地将这个概念融入其理论体系之中,将之与内在理性力量对外在感性压迫的抵抗结合起来进行解释,并将数的崇高与纯粹理性、力的崇高与实践理性相结合,从而使他对崇高的解释与其哲学体系结合成一个整体。
这种从体系出发的美学,在黑格尔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黑格尔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他从理念与感性显现的关系角度,阐释了美与艺术的关系,将艺术分成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并以此说明艺术发展的历史逻辑。他还进一步从理念与感性显现的关系出发,说明不同艺术的分类。这便是“美学”这个学科的典型构成路径,即从理论的概念和框架出发,实现理论体系的构建。
中国也有许多美学类著作,有些是理论著作,讲求理论上的整体性;也有些是教材,适应教学的需要;还有一些著作介乎二者之间。理论著作致力于建构学术体系,而教材致力于建构学科体系。李泽厚的《美学四讲》分别讲“美学”“美”“美感”“艺术”,其中每一讲又各分四个部分,显得很整齐。正如李泽厚所说,《美学四讲》由他之前发表的文章和讲演录剪贴而成,是“应读者要求而‘系统’”,而不是按照他原有的理论思路展开。李泽厚的理论思路集中体现在他于1956年发表的第一篇美学文章《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之中,即从美感开始,进而谈美和艺术。与之相似的还有朱光潜、黄药眠、吕荧和高尔泰等人的美学思想,也都是从美感谈起,逐步建立美学体系。如朱光潜早年的美学著作《文艺心理学》,讲述的是关于文艺欣赏的心理学问题;黄药眠则十分重视巴甫洛夫的心理学。与他们相反,蔡仪坚持反映论的观点,认为美是客观存在,而美感是对美的反映,即美在先,美感在后。
至此作一个总结。首先,美学是哲学的一部分,美学体系是从哲学体系引申而来的,与哲学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美学从其诞生的时刻起,就特别重视内在的结构完整性。美学家们常常从一些基本的理论预设出发,推导出美学的理论体系。再次,在美学体系建构过程中,常常吸收既有的美学概念,但这是一种体系化的吸收过程,要使概念服从于体系。最后,美学建构也要适应学科建构和教学安排的需要。应该先有美学原理,后有美学教材;先有美学的学术体系,后有美学的学科体系。众所周知,德国学者鲍姆加登最早提出要建立美学学科。其后,从康德到黑格尔,许多人都致力于建立美学体系。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西方人提起美学,都会说那是德国人发明的学科。之所以说美学具有德国色彩,就是指它有着追求建立体系的色彩基调。更为准确地说,美学总是先建立学术体系,或追求理论严整性的体系,然后才有学科体系,即综合本学科的内容,形成学科教材。
二、“艺术一般”的形成与艺术学体系建构
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艺术都是与工艺结合在一起的。《佛罗伦萨史》一书中记载,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有很多行会,这些行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手工业者的利益。在那个时代,艺术与工艺没有什么区别。石匠、木匠、铁匠等各种匠人的地位,与做绘画和雕塑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在工匠中地位高的人分为几种:第一种是首饰匠,他们处理贵重金属,与王公贵族打交道,能制作精美的首饰,甚至能做王冠;第二种是钟表匠,他们做的是可以计时的精密仪器;第三种是磨镜片的人,他们磨出镜片,可让近视的人看清书上的字,还可让对天文感兴趣的人看清天上的星星。然而,那时还没有这样一种意识,即挑出几种工匠,称他们是艺术家,或认为他们与其他的工匠不一样。
其实最早的“艺术”组合是一些活动的组合,跟“美的艺术”的组合没关系。例如最早的希腊人在酒神祭祀的仪式上唱歌、跳舞,构成了诗乐舞的组合,后来发展成戏剧。希腊人在建筑中安放雕塑,在陶瓶、陶罐上绘画,这成为后来各种造型艺术的结合。然而,这还不是美学意义上的组合,仅仅是在活动中的组合。这时,并不是由于服从于某一条美学原理而形成组合,仅仅是一些人在一起共同做了某件事。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读的《诗经》,是印在书本上的文字。而先秦时期,《诗经》的呈现方式并非如此。《诗经》要一唱三叹,合乐演奏,还有舞者跳舞。这种演出形式与礼乐制度联系在一起,是周代社会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诗乐舞的结合,也是一种活动的组合,而不是美学意义上的结合。它与现代所寻找的建立在“美”的观念上的组合,是不一样的。诗乐舞的组合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左传》所记载的“季札观乐”。为什么是“观乐”而不是“听乐”?原因就在于,季札所欣赏的是表演,是一场诗乐舞合在一起的表演。在这场表演中,诗乐舞成为表演的成分。到了后来,中国文人对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这也不是美学意义上的组合,而是指高雅的社交活动所需要的一些才能。至于文人画的诗书画的“三绝”——在画作上题诗写字,形成作画者将不同艺术门类的才能集中呈现在一部作品中的情况。这仍然与夏尔·巴托所讲的依据“同一原理”而结合的艺术不是一回事。巴托所提出的组合,是根据一个美学原理所进行的组合。这个美学原理,就是“模仿”。于是,巴托的“美的艺术”经后人不断修改、扩充,并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丰富和发展。我们今天所谈的艺术,就是从“美的艺术”组合演化而来的。
上述内容对现代艺术体系的形成,具有启发作用。但从性质上讲,它们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差别。只有那种从艺术性质上寻求内在一致性的艺术结合方式,才与现代艺术体系所追求的各门艺术的一致性,有相似之处。古罗马时期贺拉斯的“诗画一律”和中国人所讲的“诗画合一”,都有这方面的含义。“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苏轼的这一表述所体现的不是活动的结合,而是在寻找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结合。《毛诗序》中讲“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也是对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美学关系的探索。
探索不同艺术门类间的关系,将它们组合成一个整体,这在欧洲直到18世纪才有明确的表达。其中最艰难的一步,是诗与画的组合和诗与乐的组合如何放在一起,形成诗、画、乐的组合。巴托的《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一书,将诗歌、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五种艺术,再加上建筑与演讲术,共同形成一种在美学原理指导下的组合。巴托致力于将这些艺术门类用一个“同一原理”,即“模仿”,组合起来。这仍然是一种建立学术体系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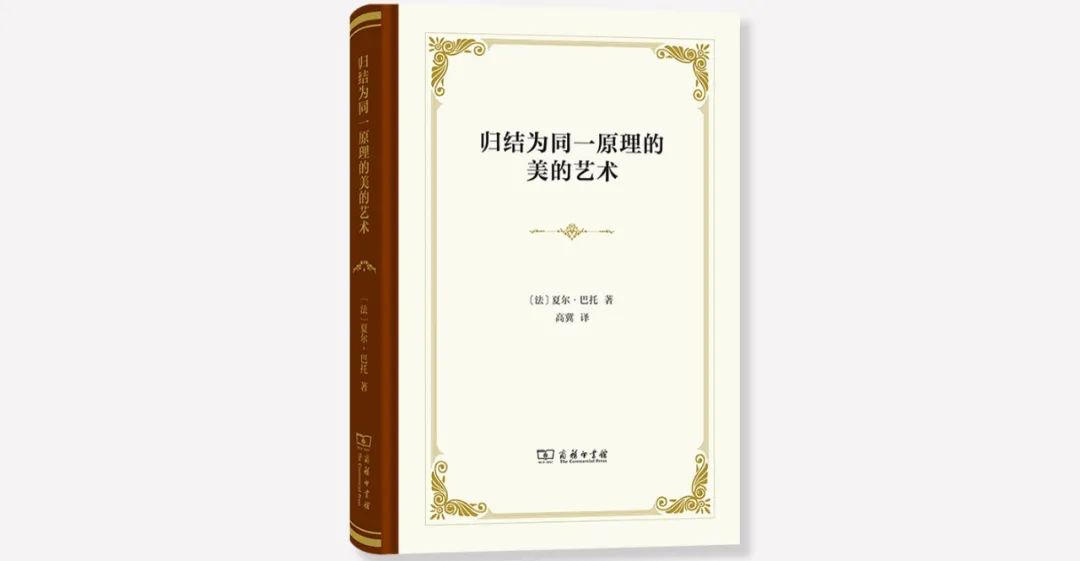 [法]夏尔·巴托:《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高冀译,商务印书馆 2022年版。
[法]夏尔·巴托:《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高冀译,商务印书馆 2022年版。
然而,巴托在两个方面的努力,即建立“美的艺术”的组合与将之归结为“同一原理”,却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命运”。在当时,形成“美的艺术”的组合的条件已经成熟,绝大多数的学者都同意设立这样的组合。《百科全书》的编者们接受了这种组合,将其用作设立、编排词条的参考。此后在巴黎,以“美的艺术”为名的教学机构也纷纷设立。与此相反,将这些艺术都归结为“模仿”这个“同一原理”的做法,却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有人认为,不同的艺术即使都是模仿,那也是不同的模仿;也有人认为,有的艺术是模仿,有的艺术并不是模仿。后来,一些认可“美的艺术”组合的人则认为,这个“同一原理”不是“模仿”。
当然,“美的艺术”名称的出现,不仅使当时正在编写的《百科全书》有关艺术类的词条的形成有了依据,而且还促成了相应的艺术教学机构,如专门的艺术类学校、大学里的艺术系、艺术研究院等机构的设立。不仅如此,美术馆、画廊、博物馆、艺术演出机构、艺术杂志,以及艺术史的研究工作等都在发展。后来,阿瑟·丹托提出了“艺术界”(Artworld)概念,围绕着这个概念产生了一场争论。乔治·迪基从“建制”(institution)角度来理解“艺术界”,而阿瑟·丹托则从观念的角度来理解它。他们的这场争论,说明18世纪开始建构的“美的艺术”概念和机制,到了20世纪已成为既定的存在,而一物是否是艺术,反过来则要由这种概念和机制来确定。迪基和丹托的观点恰恰说明,“模仿”可以被否定,“表现”也可以被质疑,“有意味的形式”也可以被超越,只有那个“建制”,或曰体制或机制决定了什么是艺术。在“美的艺术”这个组合的推动下,一种建制性的机构和机制得以形成。在“美的艺术”中,最初是由“美”而形成艺术的组合,即在“美”的名义下,将艺术与工艺区分开来。到了丹托的时代,“美”与“艺术”分离了。“艺术”仅依托机制与观念而存在,由此形成“艺术界”。先锋派艺术,例如杜尚的《泉》和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它们能够成为艺术的原因,与它们的外观无关,只与“艺术界”有关。于是,以“美”的名义所形成的“艺术”的组合,至此只要“艺术”而不要“美”了。这都是一种艺术上的“后现代性”追求所致。未来“美”与“艺术”是否会永久分离?将来会不会只有“艺术”而没有“美”?这样的“艺术”是不是会终结?这些都是当代艺术所面临的问题。当然,这一切都会过去,“美”和“艺术”还会以新的方式结合,艺术也不会终结。
三、美学和艺术学体系建构路径的异同
与之相反,艺术学先建立的是学科体系。首先是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艺术发展过程中实现组合,进而试图为这种组合寻找“同一原理”;其次是“美的艺术”,这个组合的意义在于,据此形成各种相应的“建制”,从而实现了艺术与工艺的区分;最后是由“美的艺术”所形成的“建制”及相应的观念,形成判定一物是否是艺术的标准,进而对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形成反作用。
当18世纪包括巴托在内的一批人推动建立“美的艺术”组合的时候,各个艺术门类在此之前早已实际存在。我们不能说,巴托创造了诗歌、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也不能说,巴托通过一本理论著作,从一个概念出发,就使所有这些艺术门类凭空出现。这些艺术门类本来就存在,巴托只是把一些原本就存在的艺术门类组合成一组,并试图为它们寻找一个“同一原理”,以此提升它们,使它们与工艺区分开来。这个“同一原理”,是他努力推动的,也是最为遭受质疑的。至于他提出的各个艺术门类的组合,后来被人们普遍认可。人们以“美的艺术”的名义建立了教学和研究机构,例如巴黎美术学院和法兰西艺术院等。这些机构的设立及艺术教育制度的形成,使许多艺术从业者和研究者有了固定的位置和研究的平台,也使艺术与工艺的区分有了体制上的保证。在巴托的“美的艺术”组合和寻求“同一原理”二者中,应该是组合在先,为组合寻找原理在后。组合长久地存在,尽管也曾被修正和扩充,而原理则不断被人推翻,新原理层出不穷。巴托所做的也只是“组合”而已,并不是建立体系,真正提出“现代艺术体系”的是保罗·奥斯卡·克里斯泰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当然,巴托对这一体系的建立是有功绩的。在巴托之前,也有人提出过类似的组合,但巴托以一本书的篇幅,详论各门艺术及其与“模仿”这个同一原理的关系,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艺术学的形成,当然受美学体系建构的影响,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原本就是“艺术一般”。“艺术一般”的形成,依赖于“美的艺术”组合的形成,也依赖于对这一组合中的“同一原理”的寻找。追溯“艺术一般”概念的起源,可以看到,原本只有具体的艺术活动,不同艺术门类的活动之间并没有理论上的连接,也不存在“同一原理”。现代社会的发展,强化艺术与工艺差别的社会要求,以及大学分科教学的需要,催生了“美的艺术”概念。“美的艺术”概念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形成艺术门类的组合,二是为这个组合而成的概念寻找“同一原理”。“美的艺术”建立的目的是与工艺进行区分。“美的艺术”概念又促进了专门的艺术机构,包括专门的艺术学校、大学的艺术系科、艺术研究机构,以及教育管理部门对艺术学科设置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应该是学科建设领先,在学科体系建设和完善的基础上,在美学的指导下,形成学术体系并发展话语体系。
鲍姆加登所命名的“美学”,意思是感性学,但他主要的讨论对象是艺术。他希望寻找到一个概念,即感性认识的完善,对各门艺术展开论述。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从美的四个契机谈起,最终归结到艺术上来。黑格尔在他的《美学》开头就说:“我们的这门科学的正当名称却是‘艺术哲学’,或则更确切一点,‘美的艺术的哲学’。”在他那里,美学就是艺术哲学。后来的分析美学学者则把美学定义为关于艺术批评的哲学。关于艺术的定义,谈得最多的就是分析美学。这些哲学修养很高的学者们讨论艺术定义、艺术本体论等问题,实际上就是把美学看作艺术哲学。还有“艺术一般”的提出者之一马克斯·德索,于1913年创立世界上最大的美学组织国际美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esthetics,简称IAA)。由此可见,美学和艺术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密切相关。
“美学”这个学科20世纪初在中国建立起来时,也集中关注艺术。王国维写《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关注的是艺术。当他讨论“古雅”范畴时,也特别申明,这是艺术的范畴。其后,朱光潜写《文艺心理学》,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文艺。将美学看成是研究美的哲学,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那场大讨论在美学界分为“主观派”“客观派”“主客观统一派”和“客观社会派”等派别。此后,人们都认为,美学就是研究美的科学,许多人宣称自己要解决“美”的“千古之谜”。
随着艺术学“升门”,关于美学和艺术学谁更重要,曾一度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艺术学在“升门”之后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艺术学门类下面有众多一级学科,一级学科下还有众多二级学科。与此相反,美学只是哲学这个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感觉,美学的发展空间太小了。这时,有人喊出一个口号,要艺术学,不要美学。诚然,从学科划分来讲,美学的生存空间的确很小,而艺术学作为一个门类,其生存空间要大得多。但其实艺术学也存在两难境地。在艺术院校,艺术被理解为操作性的,是为了从事绘画、雕塑、音乐和舞蹈实践工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大多不是去当作家,而是从事关于文学的史、论、评研究,然而在艺术院校,史、论、评研究并不占主要地位。可以说,艺术学背后的依托,应该是美学,没有美学依托,艺术学不能成立。
因此,作为学科的美学的设立,也是很重要的。当学科建立,设立了职位,便可以任命美学教授专门从事美学研究,美学知识也就有了生产地。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学尽管最初是作为一个学术体系建立起来的,但它跟学科的建立也并非没有关系。可以说,美学是以理论为依托,或者说以美学学术体系为依托,建立起它的学科体系的。艺术学体系是将不同门类的艺术结合成一个整体,从而形成“艺术一般”。艺术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体系不断得到丰富。在巴托那里,艺术只是一个“5+2”的体系。后来,出现了电影、电视艺术,这些都可以被纳入这个体系。包括现在的短视频、电子游戏是不是艺术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会不断出现。我们讨论艺术的边界问题,也就是在问这个体系的界限在哪里?一些过去不被认为是艺术的大众文化现象,后来都成为艺术了。过去,网络文学不被看成是作为艺术门类之一的文学。但网络文学在不断发展,最终迫使文学理论研究者关注它,并承认它在艺术体系中的地位。艺术体系被迫把很多过去不属于艺术的东西收入体系内。
民族、民间和大众艺术也是如此。“美的艺术”组合刚建立之时,致力于区分艺术与工艺,确立高雅艺术的地位。后来,艺术体系出现了反向的运动,将民间艺术和大众艺术收入其中,使艺术体系得到扩大。当代艺术理论界出现了一个热点的话题,这就是关于艺术边界的争论。艺术的边界不断扩大,甚至出现了一种“所有人都是艺术家,所有作品都是艺术品”的提法。对此,笔者认为,艺术的边界是移动的,会有越来越多的事物被纳入艺术之中。但是,这不等于艺术的边界消失。艺术的边界会被不断重建,形成新的艺术概念和艺术组合,建立新的艺术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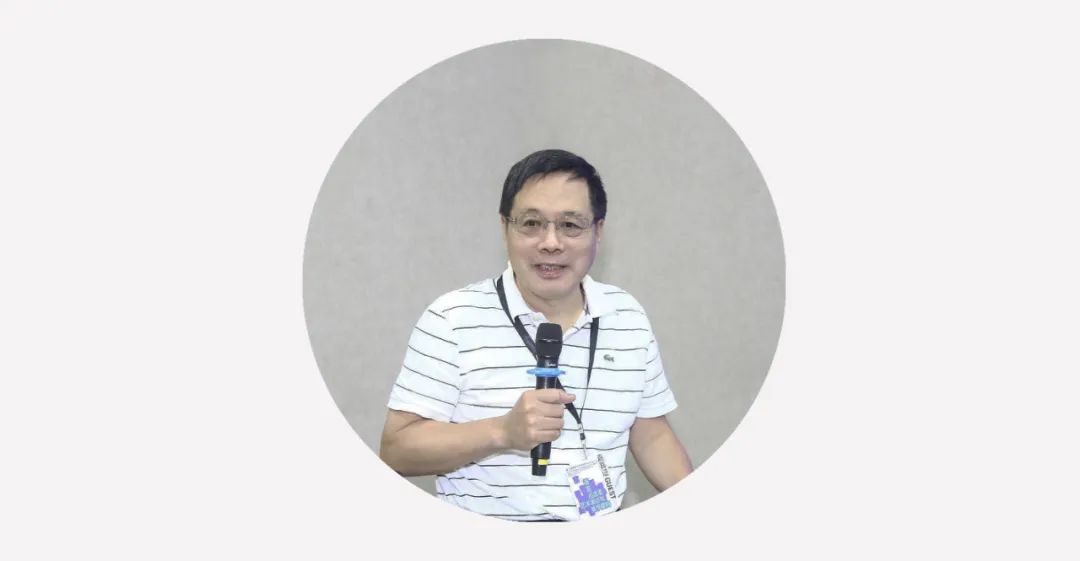
高建平,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艺术学研究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